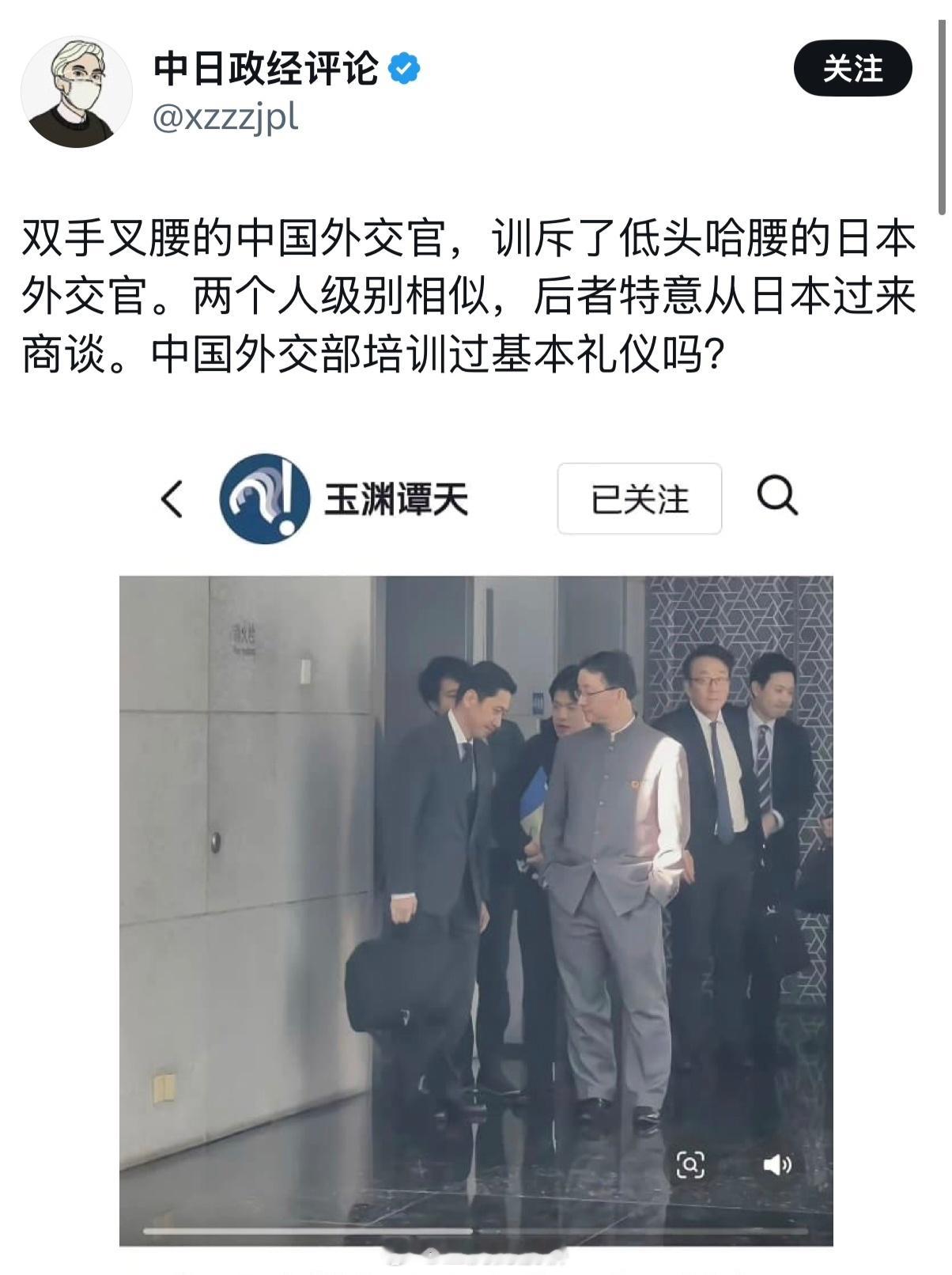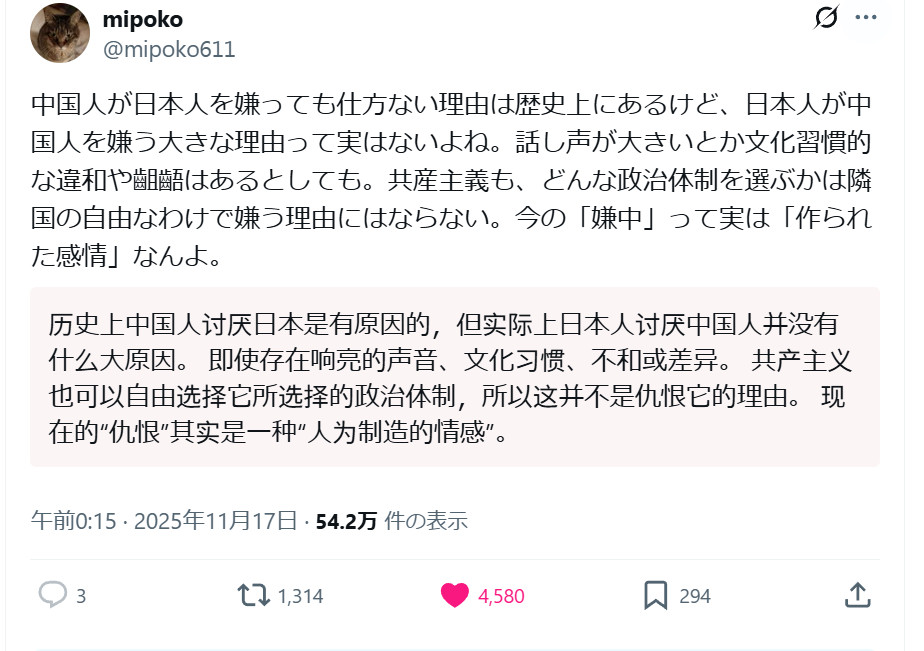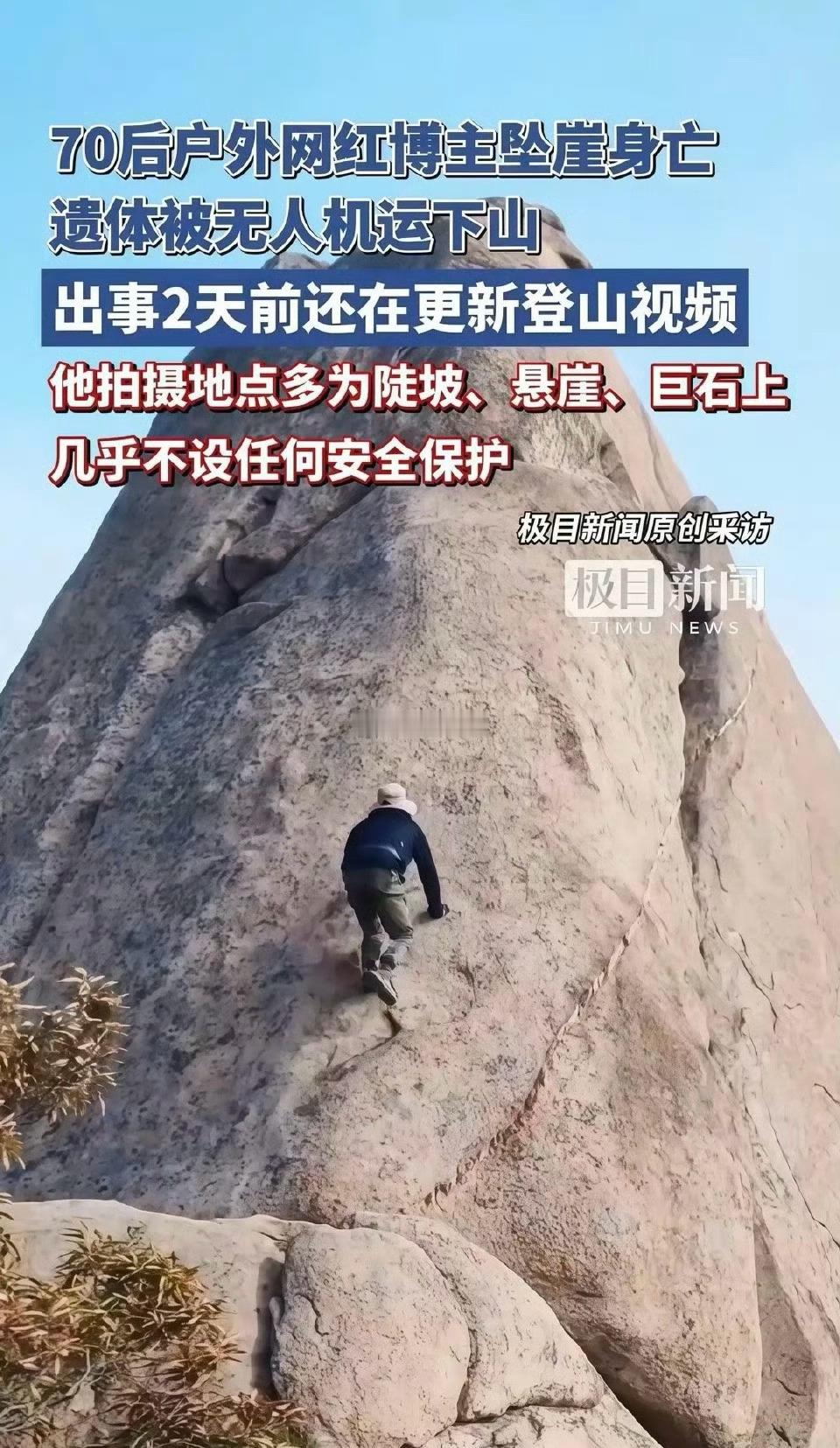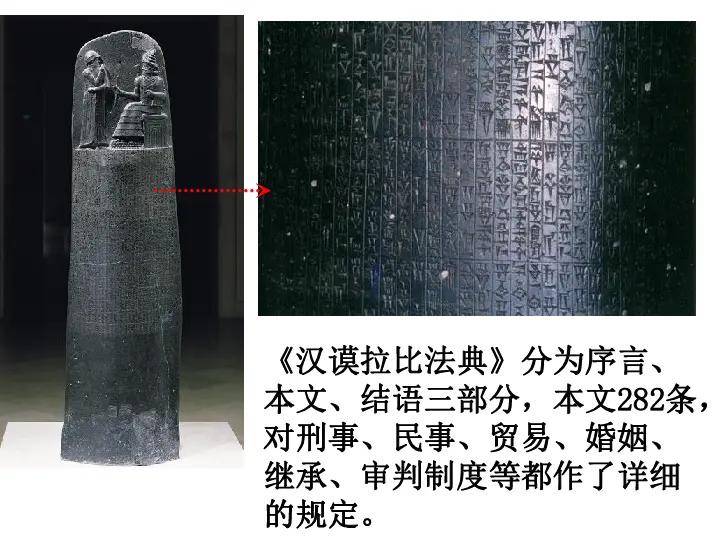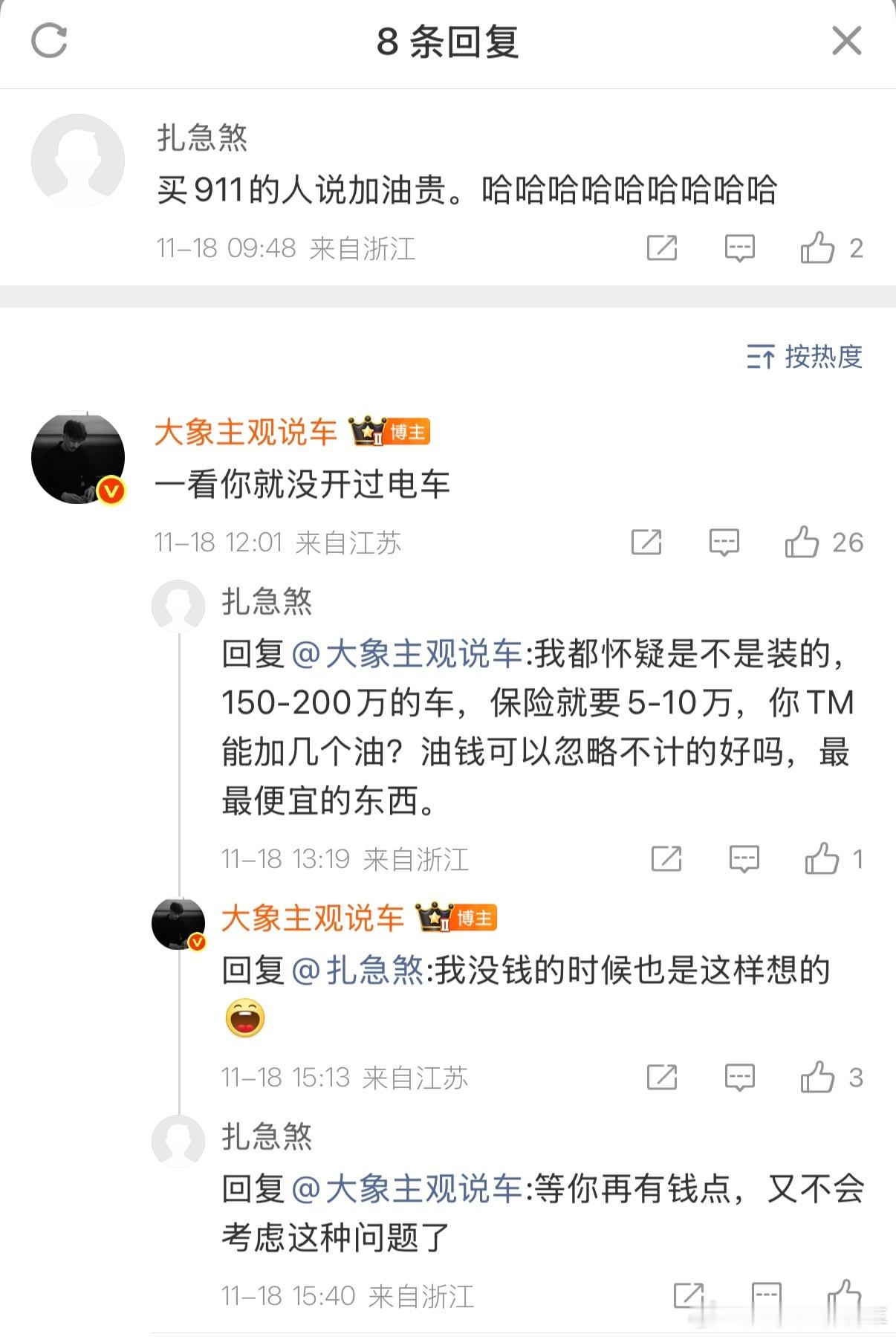1975年5月,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停在北大西门,将49岁的古典文学副教授芦荻接走。她以为只是去中南海讲几首唐诗,可怎么也没料到,这趟看似普通的出行,竟开启了长达124天的“特殊答辩”! 在北大西门停着的黑色轿车突然启动,车里坐着49岁的古典文学副教授芦荻。 他以为只是去中南海讲几首唐诗,可直到车子拐进菊香书屋的巷口,他才意识到这一去,要陪一位82岁的老人,读遍古今,辨明书里的“活气儿”。 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毛泽东正翻《刘禹锡集》。 他指着“沉舟侧畔千帆过”问芦荻:“沉舟是谁?千帆是谁?” 没等回答,自己先给出了答案:“沉舟是旧制度,千帆是人民。诗人要是只写景物,这诗就没了魂。” 这句话像锥子扎进芦荻心里。 她教了二十多年古典文学,从没想过把诗句直接拽进现实。 接下来的日子,她才懂毛泽东读书从不是“为读而读”,而是要找“能用的道理”。 有次讨论间隙,他突然拿出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校样,指着封皮铅笔写的“诗不宜注”说:“诗加了注,就成了钉在纸板上的标本,飞不起来。” 后来芦荻才知道,外文局筹备英译版时,他坚持只留必要背景,亲审的注释不到2000字。 1180首诗词、378阕词,他敢给自己的“全集”做“减法”。 因为他信读者能从字缝里读出自己的悟。 除了诗词,毛泽东对史书的研读更显“较真”。 聊到《资治通鉴》里唐肃宗奔蜀的段落,芦荻随口提了句司马光的写法,毛泽东立刻引用《旧唐书·玄宗纪》纠正:“司马光叙事太松,漏了关键细节。” 他说自己把《通鉴》读了17遍,“每一遍都在找史家的破绽”。 他还让芦荻读《晋书》,理由直白:“魏晋风度藏在恶文里,文饰越差,人性越真实。” 为了证明,他从书柜底层搬出20本毛边册。 旧报纸糊的封面,页眉页脚全是批注。 蓝铅笔记典故,红圆珠笔标制度,黑钢笔写着“此论甚陋”“司马光是书生之见”。 芦荻偷偷数过,仅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批语,就超过4万字,抵得上四篇博士论文。 这些批注不是“吐槽”,是他在书里“找活的历史”。 不是记年份,是看制度怎么变,人性怎么藏。 读小说时,毛泽东的视角更“戳人”。 他看《红楼梦》,不看宝黛的爱情,盯着“制度与人性的拧巴”。 批贾琏的泪是“怕事而非痛人”,说贾政哭贾珠是“无力而非哀子”。 评林黛玉“才气高,心志弱”,贾宝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是弱者”。 芦荻问他为什么总把悲剧读成力量,他说:“文艺要是只让人哭,就没出息。得让人哭完,知道该怎么活。” 连读《左传》这种史传,他都要抠细节。 芦荻把“卿”念成qīng,他立刻打断:“官名得读qìng,有固定读音。” 有时芦荻翻书慢,他就站起来背庾信的《枯树赋》。 四百多字,一字不差,背完说:“攻书要到底,不动笔墨不读书。” 这句话芦荻记了一辈子。 她后来在日记里写:“以前读书是‘翻完’,现在是‘抠透’。” 1976年9月6日,是两人最后一次深谈。 毛泽东让芦荻对照读《三国志》《晋书》,再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然后问:“你信哪本?” 芦荻答不上来,他拍着记录本说:“历史没有真理,只有逻辑。要学会给任何权威挑刺,挑到它站不住脚,再找能站稳的支点。”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就像打开了芦荻的“读书门”。 以前她教学生“记标准答案”,现在懂了,要教“怎么质疑,怎么找答案”。 三个月后,毛泽东病重,这段对话戛然而止。 芦荻躲在北大地下室哭了三天,随后用了10年整理60万字侍读笔记,出版《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和毛泽东谈历史与古代文学》。 扉页上写:“我只是记录了主席学问之海的一朵浪花。” 1985年,她创办“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 因为毛泽东说过:“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自己的性命。” 10年后,她在海淀路制止虐猫,冲上去夺下棍子,只说:“那年有人教过我,鸟不可动。” 2015年,85岁的芦荻把14册毛泽东亲笔批注的线装书捐给国家图书馆。 捐赠函最后一句:“它们不属于我,属于所有想知晓‘何以中国’的后人。” 毛泽东的渊博,从不是因为记性好,是因为“方法对”。 带问题读,对着不同说法比,专挑不合理的琢磨,最重要的是,读完要“用”。 芦荻后来的学生常问:“主席的读书精神,对我们有什么用?” 她总是说:“不是让你背他的批注,是让你学会‘把书读活’。 读唐诗能懂人民的力气,读史书能辨制度的得失,读小说能看人性的复杂。 最终,让书变成你‘看世界的尺子’。” 124天很短,短到只是历史的一个逗号。 124天很长,长到够让一位教授用一辈子践行“读书的方法”。 就像芦荻说的:“主席没给我们现成的答案,但给了我们找答案的勇气,敢质疑,敢对比,敢把书里的道理,变成脚下的路。” 主要信源:(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