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作家周扬回乡探亲,顺道去看前妻吴淑媛墓。谁料,半路突然雷雨倾盆,顿感慌张,立马转身离开,不敢去坟前。 没人知道,这份慌张从来不是怕打雷淋雨。彼时68岁的周扬,头发已染霜白,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来得及撑开的黑布伞,裤脚沾着泥点,背影佝偻得不像那个在文坛叱咤风云的理论家。他怕的,是坟前那片寂静里,藏着的几十年亏欠——是他这辈子都没勇气面对的愧疚。 回溯到1928年的上海,25岁的周扬还是个热血青年,在党组织安排下结识了吴淑媛。她是进步学生,眉眼清秀,写得一手好字,不仅帮他抄写革命文稿,还悄悄变卖首饰资助地下工作。两人在法租界的小弄堂里结了婚,没有仪式,只有一张写着“同心革命”的红纸贴在墙上。那些日子,周扬白天躲在阁楼翻译进步书籍,晚上和吴淑媛挤在窄床上,听她讲家乡的稻田,讲未来的日子。“等革命成功了,咱们就回绍兴,守着爹娘,种几亩地。”吴淑媛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周扬却只是搂紧她,没敢应承——他知道,革命这条路,从来由不得儿女情长。 1930年,周扬奉命前往中央苏区,临走前夜,吴淑媛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眼泪掉在他的衣襟上。“我等你回来。”她塞给他一双亲手纳的布鞋,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是她熬了三个通宵的心血。周扬接过鞋,喉头哽咽,只说了句“照顾好自己”,便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他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分离,却没料到,这一去,竟是天人永隔的开端。 到了苏区后,战火纷飞,通讯中断,周扬和吴淑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曾托人打听妻儿的消息,却只收到“战乱中失联”的回复。后来,他投身文艺战线,忙于抗日宣传和文化建设,在颠沛流离中又组建了家庭,女儿的笑脸和吴淑媛的模样,渐渐被繁重的工作压进了记忆深处。可他不知道,吴淑媛带着女儿,在白色恐怖中东躲西藏,既要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又要拉扯孩子长大。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精神紧张,让她身体日渐虚弱,1941年,年仅38岁的吴淑媛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前还攥着那半张当年的红纸,反复念叨着周扬的名字。 这些往事,周扬是直到建国后才知晓的。当年受他所托打听消息的老战友,辗转找到了他,把吴淑媛的遭遇和临终遗言告诉了他。那一刻,这个在风浪中从未退缩的硬汉,突然蹲在地上痛哭失声。他才知道,自己当年的“身不由己”,在吴淑媛那里,是一辈子的孤苦等待;自己后来的“功成名就”,背后藏着一个女人耗尽生命的坚守。这些年,他无数次想回乡祭拜,可每次临近家乡,都迈不开脚步——他怕面对吴淑媛的墓碑,怕那双曾充满期盼的眼睛,更怕自己无法原谅那个失信的、自私的自己。 这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像是上天特意安排的考验。雨水模糊了前路,也模糊了周扬的视线,他仿佛看到当年吴淑媛送别时的身影,看到她在灯下纳鞋底的模样,看到她临终前期盼的眼神。雷声轰鸣,像是吴淑媛无声的质问,又像是他内心的谴责。他转身就走,脚步踉跄,伞都忘了撑开,任凭雨水打湿全身。他不是逃,是不敢面对——面对那个被自己辜负的女人,面对那段被时代洪流裹挟、却终究留下遗憾的过往。 有人说周扬薄情,可谁又能真正体会,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多少人的个人情感,都只能让位于家国大义?他不是不爱,只是在革命与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他不是不想念,只是这份想念,被岁月和愧疚压得太深。晚年的周扬,常常在深夜翻看吴淑媛当年写的信,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依旧清秀,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他整夜难眠。他曾对身边人说:“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正确的选择,唯独对吴淑媛,我错得彻底。” 这场雷雨,终究没能让他迈出那一步。或许在他心里,保持一份距离,留下一份遗憾,也是对吴淑媛的一种亏欠式的尊重。有些愧疚,注定要用一辈子来背负;有些遗憾,注定要成为生命里无法弥补的缺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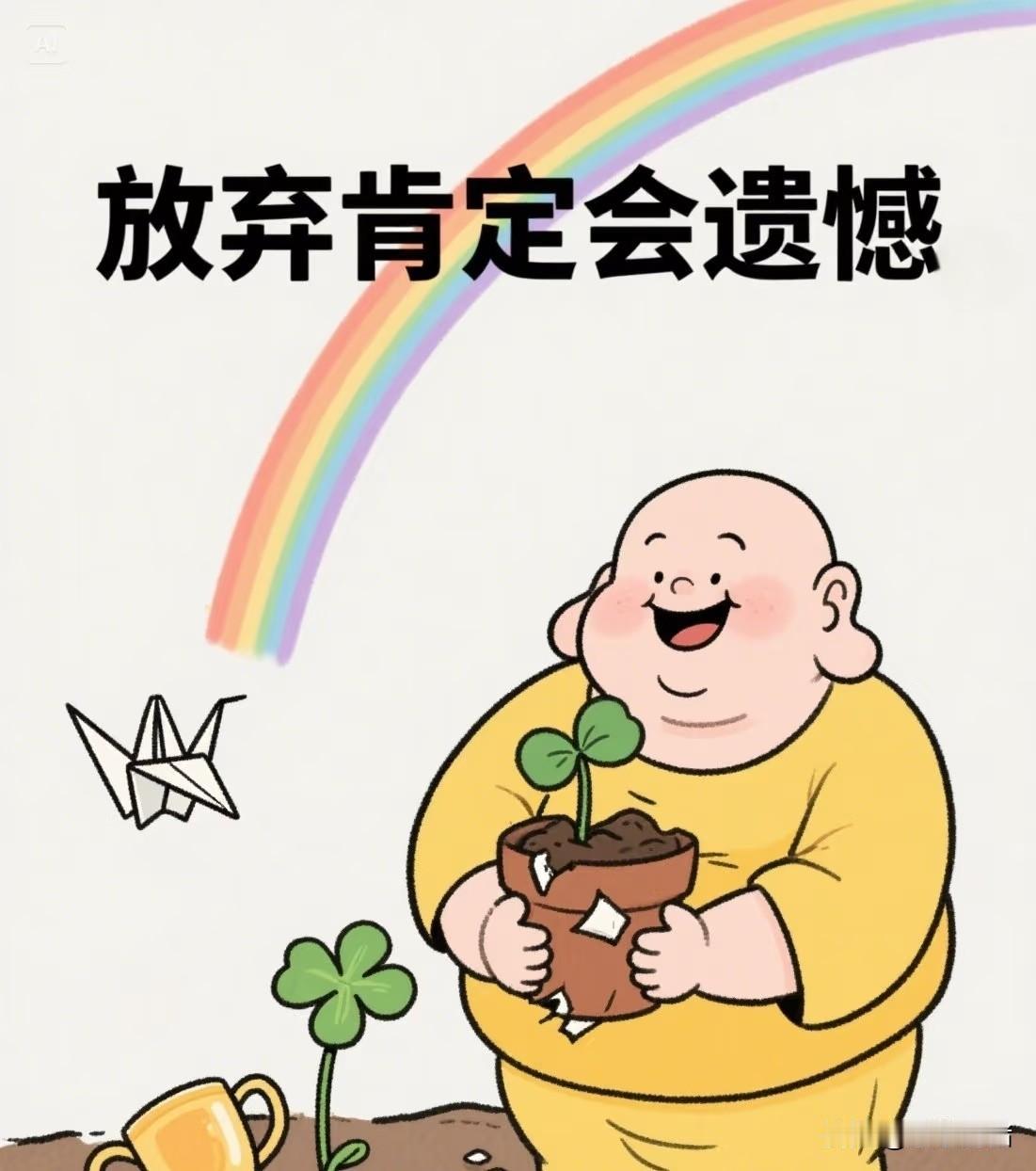



![榜一大哥该哭死在卫生间了吧是一个人吗?网红原来是人贩子[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208380413953750574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