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对未知的恐惧。 人生如“生”字拆解——牛在土上,背负沉重轭具,一生低头耕犁。三十岁时,我们开始学习与未知的恐惧对峙;四十岁稍能看清迷雾轮廓;五十岁明白肩上犁痕皆是命定沟壑;六十岁连逆耳风声都听成韵律;七十岁方能在尘世规则里走出自在的足迹。 这头地上的牛,吃尽四季苦草,踏碎晨昏霜露,碌碌蹄印终被新土覆盖。最深的惧,不在耕耘之重,而在最后一垄犁完,暮色四合时——那垄沟尽头究竟是荒芜,还是另一片待垦的黎明? 未知如夜色浸透每寸泥土,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终”,而是终章之后,那没有牛轭也没有草香的、绝对的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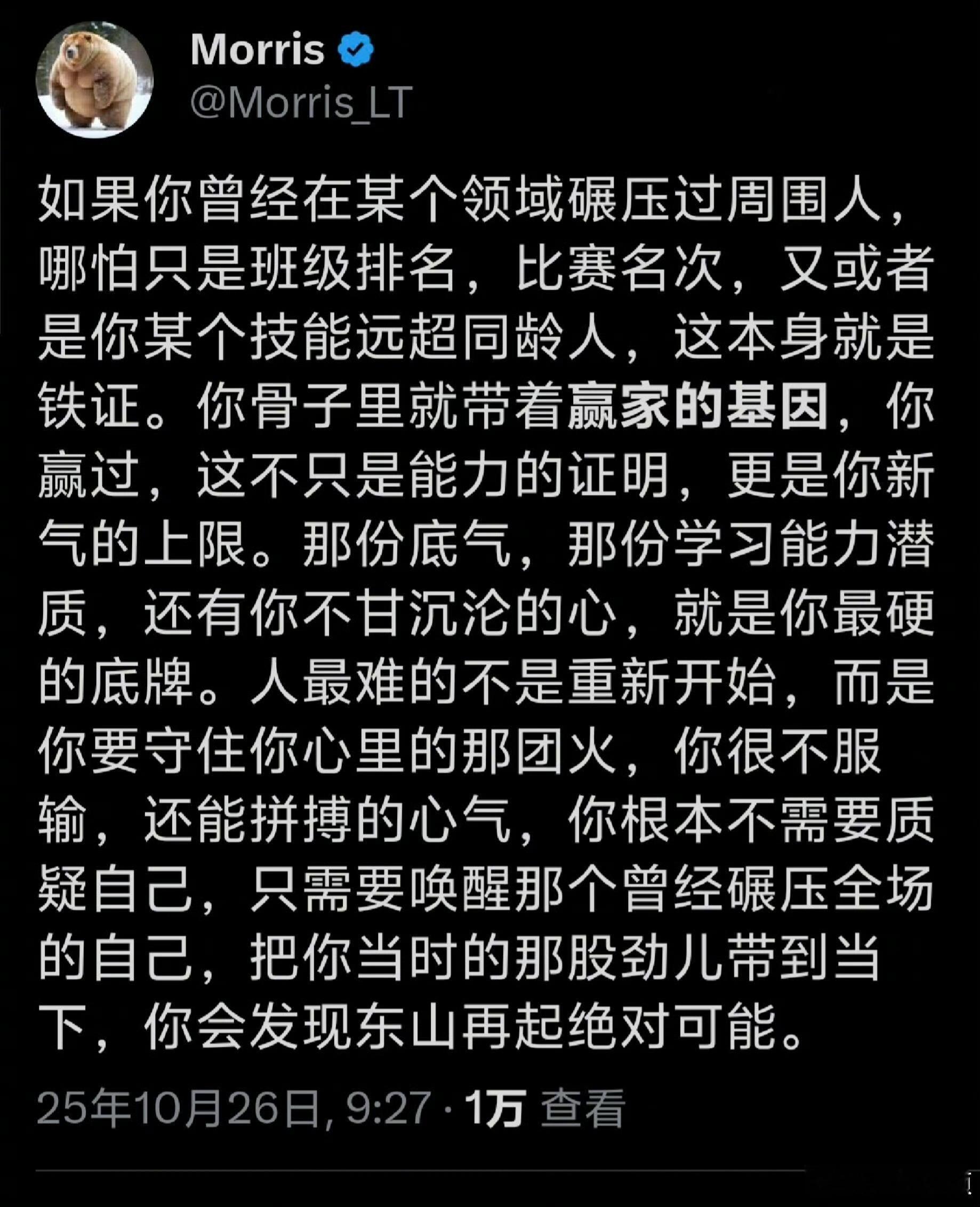

![一切都是命[祈祷]](http://image.uczzd.cn/132378488625555774.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