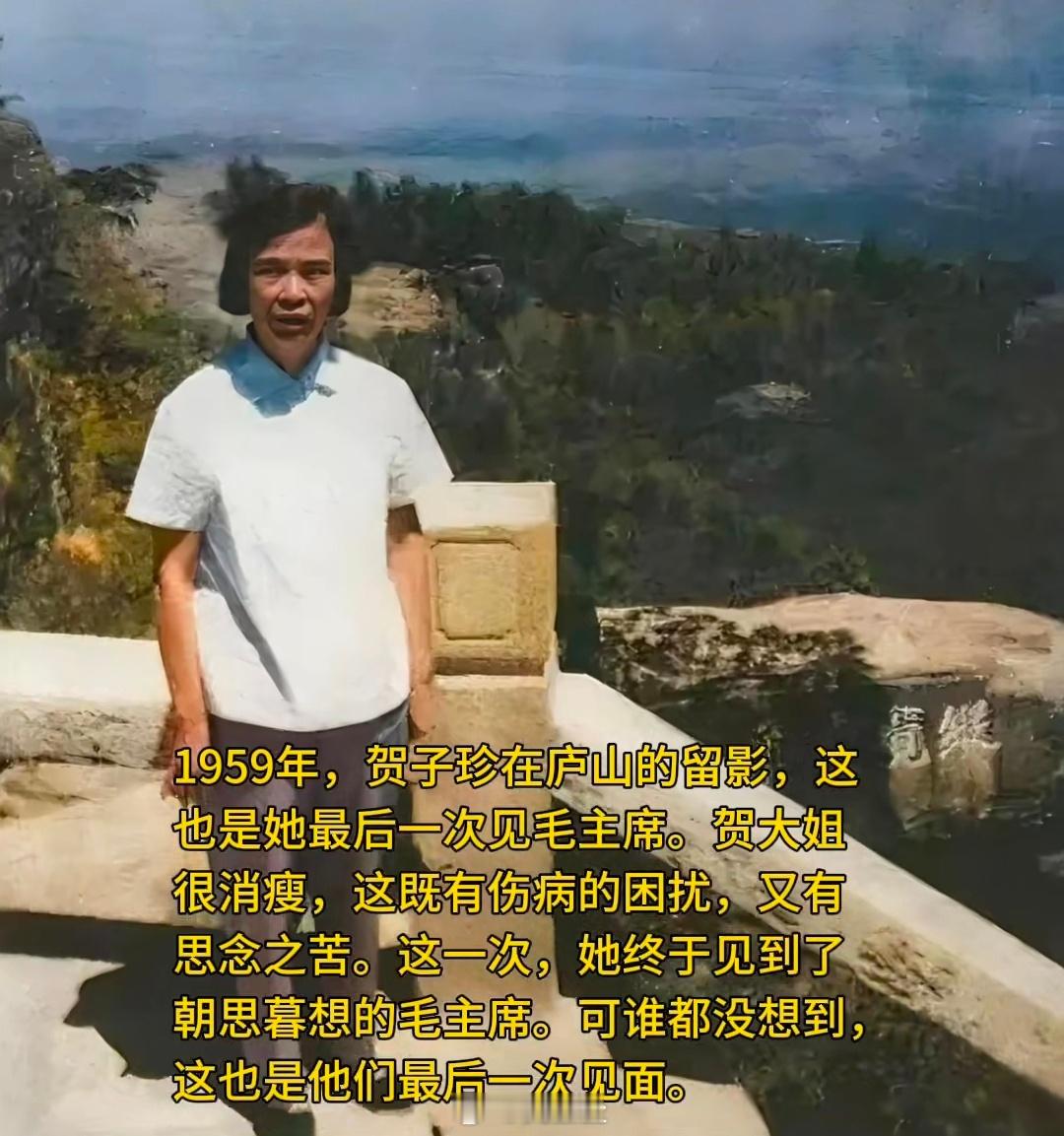1936年,联络员陈宏叛变,敌人利用陈宏,诱骗陈毅下山,陈毅不知情。下山时,陈毅因口渴向少妇讨水喝,少妇一句话,竟救了他一命! 1936年,的中华大地正处于剧烈动荡的前夜,虽然北方的西安传来了蒋介石被扣留的惊人消息,整个局势波诡云谲,但在南方的油山地区,战争的迷雾从未散去,自1934年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后,留守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就陷入了“卧榻之侧”的险境。 对于陈毅和项英而言,比肉体上的伤痛和物质上的匮乏更可怕的,是信息的彻底隔绝,他们就像两叶扁舟,失去了灯塔的指引,既不知道党中央的具体方位,也难以判研外界真实的政治风向。 正是这种对“中央指示”的极度渴求,被敌人精准地捕捉到了,织就这张大网的人叫龚楚,这个名字对于老红军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参与领导过百色起义,资历极深,甚至担任过红七军的参谋长。 然而,这位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了最了解红军弱点的对手,龚楚太清楚陈毅的心理防线在哪里,那是对组织联系的迫切向往,为了将陈毅引出深山,龚楚没有选择硬攻,而是打出了一张名为“信任”的牌。 他盯上了陈毅的联络员陈宏这个联络员不仅熟悉梅岭一带如迷宫般的地形,更是陈毅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每次下山,陈宏都能带回物资和报纸,从未出过差错,龚楚正是利用了旧日首长的身份威逼利诱,轻易撕开了这道防线。 当叛变后的陈宏带着那封声称“中央特派员在大余县接头”的密信进山时,陈毅心中的防备其实已经被对组织回归的渴望冲淡了,在陈毅看来,既然信是老战友龚楚的笔迹,送信人又是生死与共的陈宏,如果这两人都不可信,那山外恐怕已无立足之地。 即便渴望重建联系,多年游击战练就的生存本能并没有完全消失,陈毅虽然接受了下山赴约的建议,但他做出了一个关键的风险隔离决定:不能和项英同时去,这一举动,在最后关头保住了南方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为了掩人耳目,这位叱咤风云的指挥官特意换上了一件褪色的旧长衫,手里或许还拿着一把折扇或几本书,将自己装扮成当时最常见的乡村教书先生,大余县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怪异。 按理说,既然有“中央特派员”到来,安保应当极其隐秘,或者局势极度紧张,但当陈毅带着一名警卫员潜入城内时,眼前的一切却显得过于“干净”平日里在街头巷尾横行的军警巡逻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面孔生疏、口音杂乱的小商贩。 这种反常的平静,不仅没有让陈毅放松,反而让他浑身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对于在刀尖上行走了三年的人来说,每一个反常的细节都是死亡的信号,然而真正决定命运转折的,并不是这些军事上的疑点,而是一次意外的“访友”。 长途跋涉后的干渴,让陈毅想到了去找联络员陈宏讨口水喝,毕竟陈宏的家就在路边,进去歇个脚显得合情合理,正是这个出于生理本能的决定,让他避开了设在饭店的主包围圈,误打误撞地闯入了真相的边缘。 推开陈宏家的大门,迎接陈毅的并不是那位熟悉的联络员,而是一位穿着讲究的少妇,陈宏的妻子,这个场景本身就充满了违和感:一个常年在此地活动的地下工作者,家中的陈设和眷属的状态似乎并不符合那个年代贫苦百姓的常态。 但陈毅不动声色,借口是“陈老弟的朋友”,只是路过讨碗水解渴,当清凉的水入喉,警卫员借故去茅房的空档,陈毅状似无意地问了一句陈宏的去向那位操着赣南口音的少妇并没有太多心机,她一边收拾着家务,一边随口答道:“他上团部去了,在那边待了好几天没回了”。 这里的“团部”,指的是国民党军的团部指挥所,也就是陈宏正在配合龚楚布置抓捕陷阱的地方,然而命运在这里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陈毅是四川人,对于当地含混的赣南土话并不精通,再加上当时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他将少妇口中的“团部”听成了“糖铺”。 这两个发音在方言中极度相似,但在陈毅的脑海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广启安”糖铺,正是大余县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按照党的地下工作铁律,联络员的家人是绝不允许知道交通站具体位置的,更不可能知道丈夫“去糖铺住了几天”。 如果陈宏连这样的保密纪律都违反了,随意告诉妻子行踪,要么是他严重违纪,要么就是那个地方已经不再是秘密,这句被“听错”的实话,像一道闪电击穿了龚楚精心编织的谎言迷雾。 警卫员回来后,陈毅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压住心中的惊雷,决定去那个“糖铺”看一眼以证虚实,当他们路过“广启安”糖铺时,眼前的景象印证了所有不祥的预感,这个平日里虽然隐蔽但依然有接头暗号的铺子,此刻却死气沉沉,店内空无一人。 甚至连柜台后换上的新老板也透着一股鬼鬼祟祟的气息,这种令人窒息的陌生感,彻底坐实了陈毅的判断:联络线断了,所谓的“中央特派员”根本就是死神的幌子,陈毅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带着警卫员转身没入人群,迅速撤离了大余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