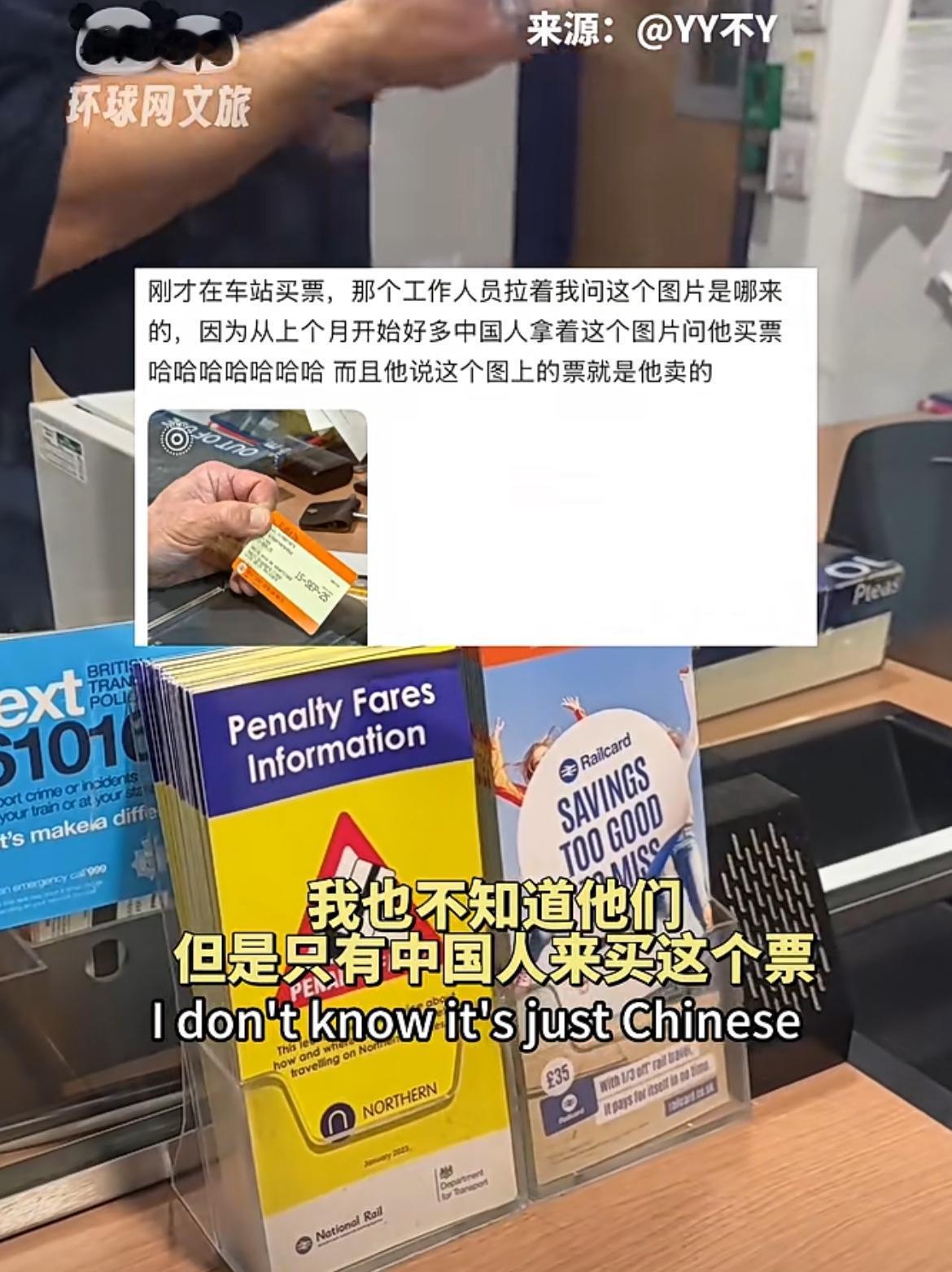1983年的秋天,某县城的河滩边围满了人。 二十多个年轻人跪在土坡上,背后的白牌子写着“流氓犯”。 人群里有人踮脚张望,有人捂住孩子的眼睛,没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枯草的声音。 不远处,几个中年妇女攥着皱巴巴的钱,等着缴纳“子弹费”。 领回的不只是遗体,还有一张盖着红章的收据,上面的数字比当时一个月工资还多。 那会儿的中国刚打开国门,南方的小商贩背着电子表往北方跑,火车站挤满找活儿的农民。 人流动起来了,麻烦也跟着来。 街面上抢钱包的、撬门的多了,甚至有拿着猎枪拦路的。 1983年夏天,“二王案”闹得全国不安,两个逃犯从沈阳一路杀到江西,公安部第一次发了全国通缉令,报纸上印着他们的照片,连小学生都能认出那两张脸。 这样的背景下,政策来得很快。 邓小平在会上拍了桌子,说要“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没多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决定,1979年刚施行的刑法里,杀人、抢劫、强奸这些罪的量刑直接往上提,连“投机倒把”都算重罪。 那会儿办案讲究效率,批捕到判决有时候就几天,法院的公告贴在电线杆上,墨迹没干就围满人看。 公开审判成了常事。 不光县城河滩,有些地方还在体育场开公审大会,犯人身后站着戴红袖章的法警,喇叭里念着罪状。 老百姓去看热闹,也是受教育,那会儿大家觉得,坏人就得这么治。 但问题也跟着来,“流氓罪”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有人因为跟异性跳贴面舞被抓,有人因为写情书用词大胆被定罪,卷宗里常看到“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这样的话。 年轻人占了罪犯里不小的比例。 那会儿刚流行迪斯科,穿喇叭裤、留长发的青年在街上走,都可能被当成“不良分子”。 严打后,少管所人满为患,后来专家调研发现,很多孩子是因为没人管才学坏的。 这才有了后来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了社区矫正,不再光靠关起来解决问题。 严打那几年,晚上出门确实踏实多了。 但后来翻卷宗,看到有个十九岁的青年因为在公园亲了对象一口被判了刑,我觉得这可能是当时最大的遗憾,用今天的眼光看,有些边界确实模糊了。 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流氓罪”被拆成了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具体罪名,罪刑法定原则终于立了起来。 那张“子弹费”收据后来被收进了档案馆,旁边放着1997年刑法修订草案。 当年跪在河滩上的年轻人如果还在,或许会看到,曾经模糊的条款已经变得清晰。 严打像一场急雨,暂时浇灭了乱象,也让后来的人明白,社会治理不能只靠速度,更要靠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