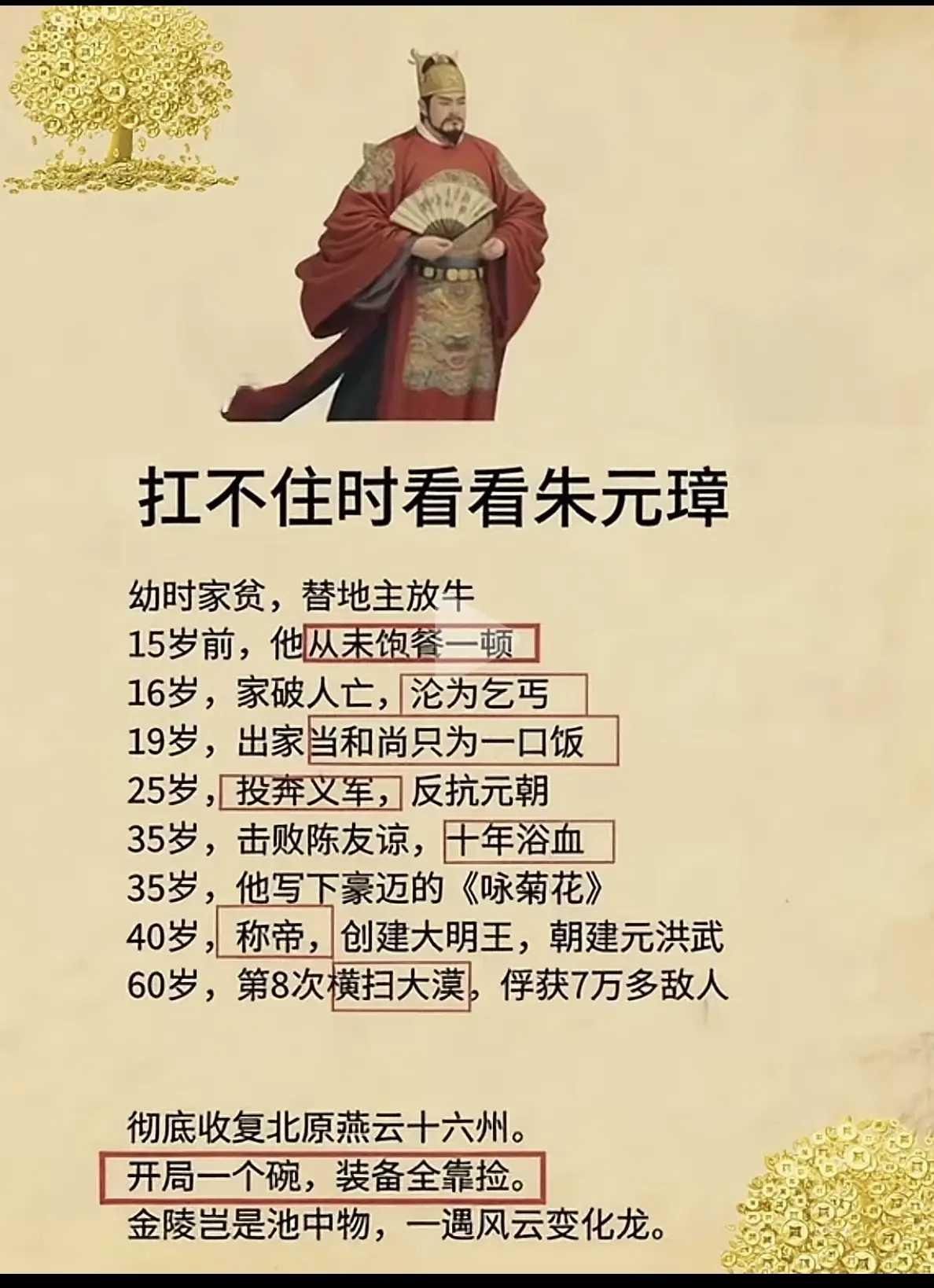1646年,田见秀率七千残兵降清,多尔衮本想安排他成大将,谁知竟因部下一句话,多尔衮直接斩杀田见秀以及三千降兵,这究竟为何? 田见秀是李自成当年最信任的“权将军”。三年前,他手握着大顺王朝的帅印,守着西安门户。李自成兵败山海关,退到西安时,曾咬着牙对他说:“玉峰,把城里的粮草全烧了!一颗米也不能留给鞑子!” 田见秀应下了。可当他站在堆满粮食的仓库前,看着外面饿得眼冒绿光的百姓,这汉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后,他只让人点着了粮库旁边一个破塔楼,几十万石粮食,一粒没动。 这堆粮食,后来成了清军的军饷。靠着这些粮食,阿济格的八旗兵像疯狗一样追着大顺军咬,彻底打乱了李自成在武昌休整的计划。第二年春天,李自成在九宫山死了,大顺的天,塌了。 现在,轮到田见秀做选择了。七千残兵,前有清军围堵,后有南明疑忌。粮草快断了,军心也散了。手下几个将领开始偷偷摸摸,想拉走自己那点人马。 “将军,降了吧。”一个亲信红着眼劝他,“再打下去,兄弟们都要饿死在这山里了。” 田见秀盯着地图,三天没说话。他想起了李自成把帅印塞到他手里那晚说的话:“西边的门户,就交给你了。”如今,这个门户,连门板都让人拆了。 “备马,我去见多尔衮。”他最后下了决心。 武英殿。三十来岁的多尔衮看着战报,嘴角难得地翘了翘。这个田见秀的名头他听过,李自成手下排得上号的人物。这样的人来降,对刚入关、脚跟还没站稳的大清来说,是块好招牌。 “给他个总兵衔,让他还带旧部。”多尔衮对身边的谋士范文程说,“正好招抚山陕那些流寇。” 可范文程,这个投靠清朝多年的汉臣,却摇了摇头:“王爷,这步棋,走不得。” “哦?”多尔衮抬了抬眼皮。 “田见秀不是一般人。”范文程声音很平,但字字像钉子,“他是李闯的心腹大将,地位和刘宗敏不相上下。刘宗敏是什么人?到死都没投降的主儿。田见秀现在来降,是走投无路,不是真心归顺。他能叛李闯,将来就不能叛大清?” 多尔衮的手指在紫檀木桌面上轻轻敲着。范文程的话,像盆冷水,浇灭了他刚才那点高兴。 “再说了,”范文程往前凑了半步,“南边还在打仗,大顺的残部已经和南明搅在一起了。留着他,万一他和旧部暗通款曲,我们岂不是养虎为患?依我看,不如……” 他做了个手起刀落的手势。 帐里静得能听见灯花爆开的声音。几个满洲王爷也纷纷附和:“刘宗敏宁死不降,姓田的这么容易就怂了,肯定有鬼!”“他那几千人,还不够塞牙缝的,留着干嘛?” 多尔衮闭上了眼。他脑海里闪过山海关的血战,闪过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大清的江山,是抢来的,坐得还不稳。他需要的不是一两个降将,是绝对的服从,是杀一儆百的威慑。 “斩了。”两个字,轻飘飘地从他嘴里吐出来,却像千斤重锤落下。 消息传到田见秀营中时,他正在擦拭一把旧刀。听了传令兵的话,他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擦得很慢,很仔细。 “将军,咱们跑吧!”几个老部下急红了眼。 “跑?”田见秀苦笑一声,“往哪跑?天下之大,已经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了。” 他想起西安城里那些等着领粮的百姓,想起李自成叫他“玉峰”时信任的眼神,想起这些年的万里征途。到头来,自己就像这手里的刀,用的时候是宝贝,不用的时候,就成了碍眼的铁片。 刑场上,雨又下起来了。田见秀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什么也没说。刀光一闪,这个曾经跟着李自成从秦岭杀出来、打下半壁江山的汉子,倒在了1646年湿冷的春天里。一起倒下的,还有他手下那三千多个相信“投降就能活命”的兄弟。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残酷。你以为自己是一枚重要的棋子,可在下棋的人眼里,你也许只是用来震慑其他棋子的——那颗被吃掉的“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