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越南。两个美军士兵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一名阵亡的北越士兵。突然,一个美军大声说:“别动他,小心有诡雷!”另一个美军吓得赶紧缩回了手。 喊话的美军叫米勒,入伍前是俄亥俄州的农场主,脸上还带着没褪干净的青涩。他的声音发颤,额头上的冷汗混着雨水往下淌,浸透了衣领。三个月前,他的战友就是在打扫战场时,碰了一具北越士兵的尸体,结果尸体下的诡雷炸响,战友的一条腿当场没了,躺在担架上的哀嚎声,到现在还在米勒的耳朵里盘旋。这片雨林是天然的战场,到处都是看不见的陷阱,北越士兵的诡雷从来防不胜防,没人敢拿命赌。 另一个士兵叫卡特,是个刚到越南半年的新兵,手里的M16步枪攥得死紧,指节都泛了白。他看着躺在泥水里的北越士兵,对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军装上全是弹孔和泥土,胸口还插着一截弹片。 年纪看着不大,顶多二十岁,脸上还沾着草屑,眼睛睁得圆圆的,望着天的方向。卡特咽了口唾沫,喉咙发干,他想起自己远在纽约的弟弟,和这个北越士兵差不多大,此刻应该正在教室里上课,而不是躺在异国的雨林里,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掩盖了远处零星的枪声。米勒慢慢蹲下身,手里拿着工兵铲,小心翼翼地拨开北越士兵身边的泥土。他的动作很慢,每一下都轻得像怕惊醒对方。卡特在旁边警戒,眼睛扫过四周的草丛,生怕从里面钻出一个北越士兵。 工兵铲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米勒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停下动作,屏住呼吸,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把那个东西扒拉出来。不是诡雷,是一个用防水布包着的小本子。 米勒松了口气,瘫坐在泥水里,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他打开那个小本子,里面的纸页有些发黄,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越南文字,还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女人穿着碎花裙子,笑得很温柔,小孩骑在女人的肩膀上,手里举着一朵野花。 本子的最后一页,用铅笔写着一行字,米勒看不懂越南文,却能认出旁边画着的小太阳。他把本子递给卡特,卡特接过,看着照片上的笑脸,突然就红了眼眶。 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个北越士兵叫阮文雄,是越南南方的一个农民。1965年,美军进入越南后,他的村子被炮火夷为平地,母亲和妹妹都死在了轰炸里。他跟着父亲加入了北越军队,临走前,妻子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来送他,他拍了这张照片,说打完仗就回家。 他从来没放过诡雷,他的背包里除了子弹和干粮,就只有这个小本子和半块没吃完的米糕。他只是一个想保护家人的普通人,却死在了异国他乡的雨林里。 米勒和卡特没有搜刮阮文雄的遗物,他们把那个小本子和照片放回他的口袋里,又用泥土和树枝,给他堆了一个小小的坟包。卡特从背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放在坟包上,那是他母亲寄来的,他一直没舍得吃。米勒对着坟包鞠了一躬,嘴里念叨着,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对不起。雨越下越大,冲刷着坟包上的泥土,也冲刷着他们脸上的泪水。 那天之后,米勒和卡特再也没有碰过任何阵亡士兵的遗物。他们见过太多的死亡,见过太多的家破人亡。他们开始明白,这场战争里没有赢家,无论是美军还是北越士兵,都是被卷进来的可怜人。他们扛着枪,在雨林里穿梭,心里却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 米勒常常想起他的农场,想起农场里的牛羊,想起他的妻子在门口等他回家的样子。卡特常常想起他的弟弟,想起弟弟写给他的信,信里说等他回家,要带他去看纽约的自由女神像。 战争从来都不是英雄的游戏,是普通人的炼狱。那些躺在战场上的士兵,不是冰冷的数字,不是敌人的代号,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他们的口袋里,装着家人的照片,装着对和平的渴望,装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家。米勒和卡特后来活了下来,回到了美国,却再也忘不了那个越南雨林里的下午,忘不了那个叫阮文雄的北越士兵,忘不了那张照片上的笑脸。 战争的残酷,从来不是枪炮的轰鸣,是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尸体,是把一个个温暖的家,变成破碎的回忆。那些在战场上失去的,从来都不是用胜利和失败就能衡量的。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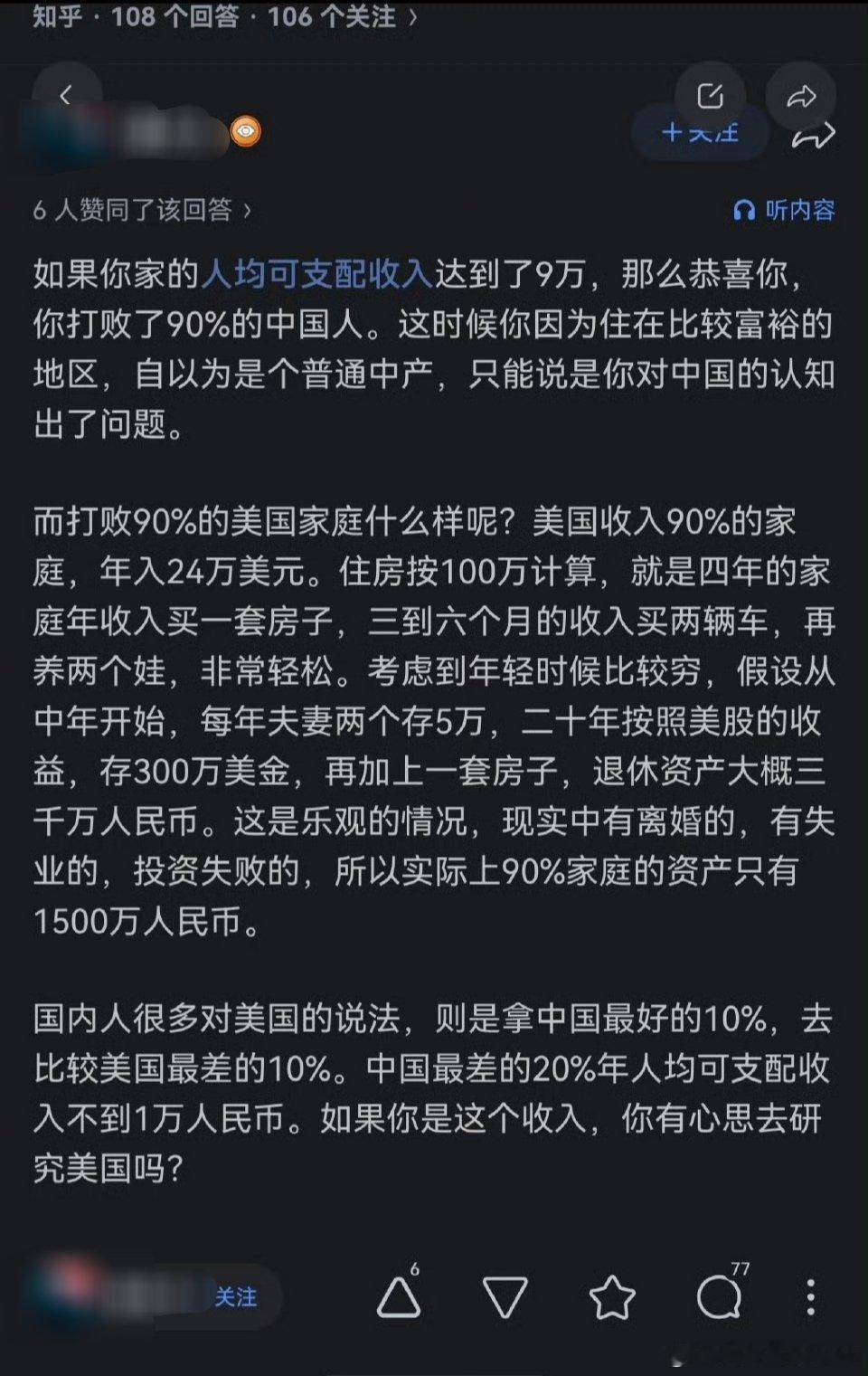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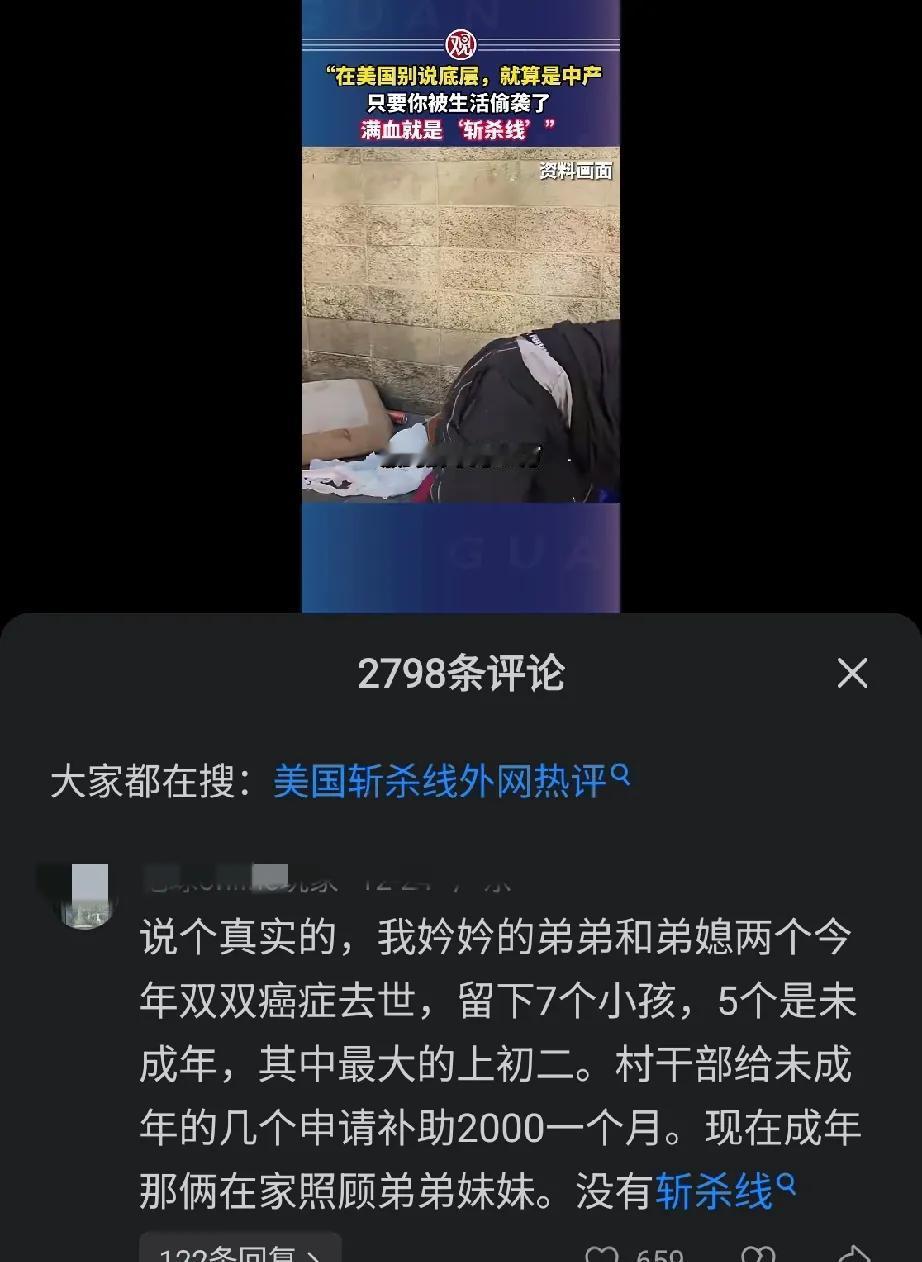
![一个愿娶,一个愿嫁,这不是都挺好[狗头]](http://image.uczzd.cn/1347679349589599696.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