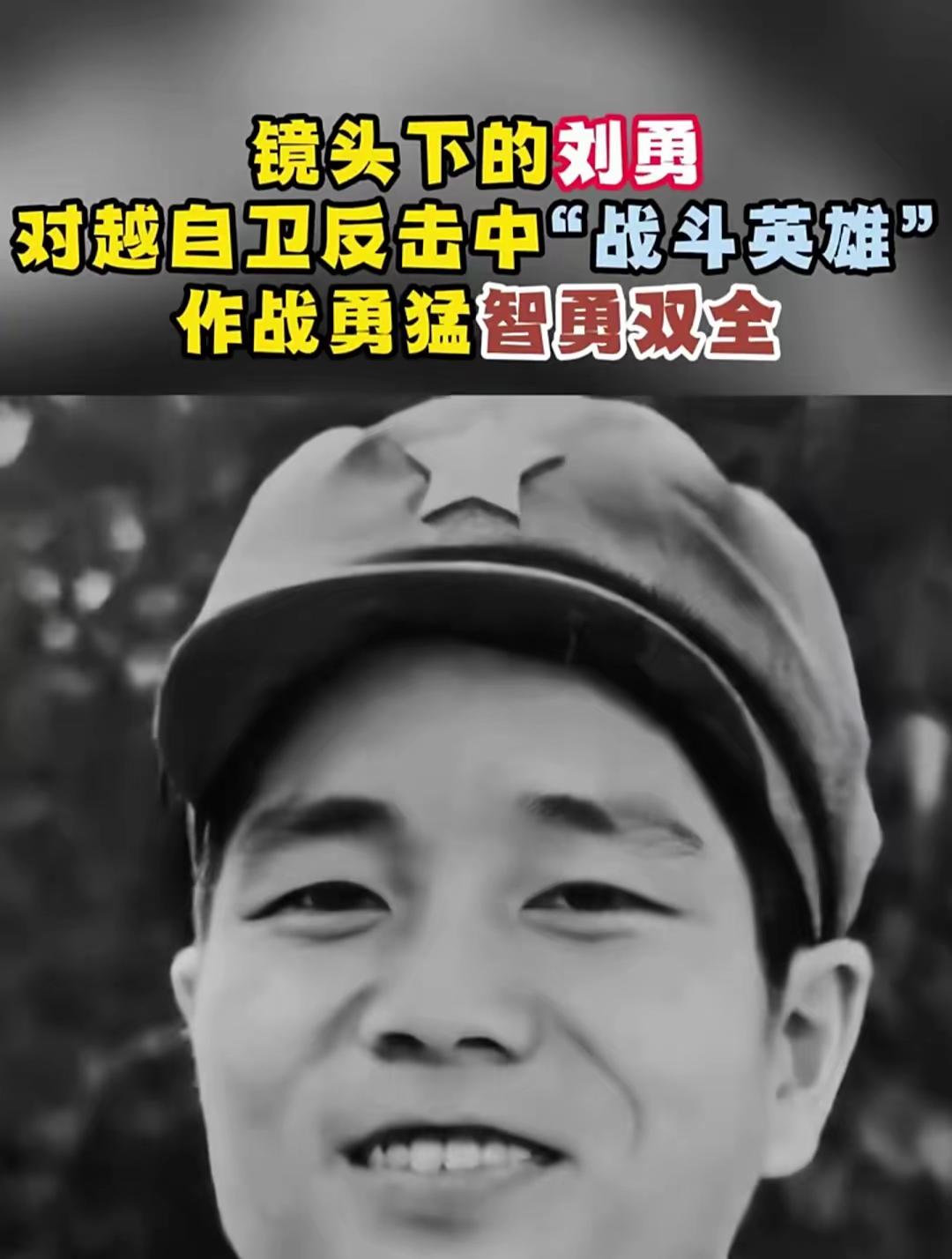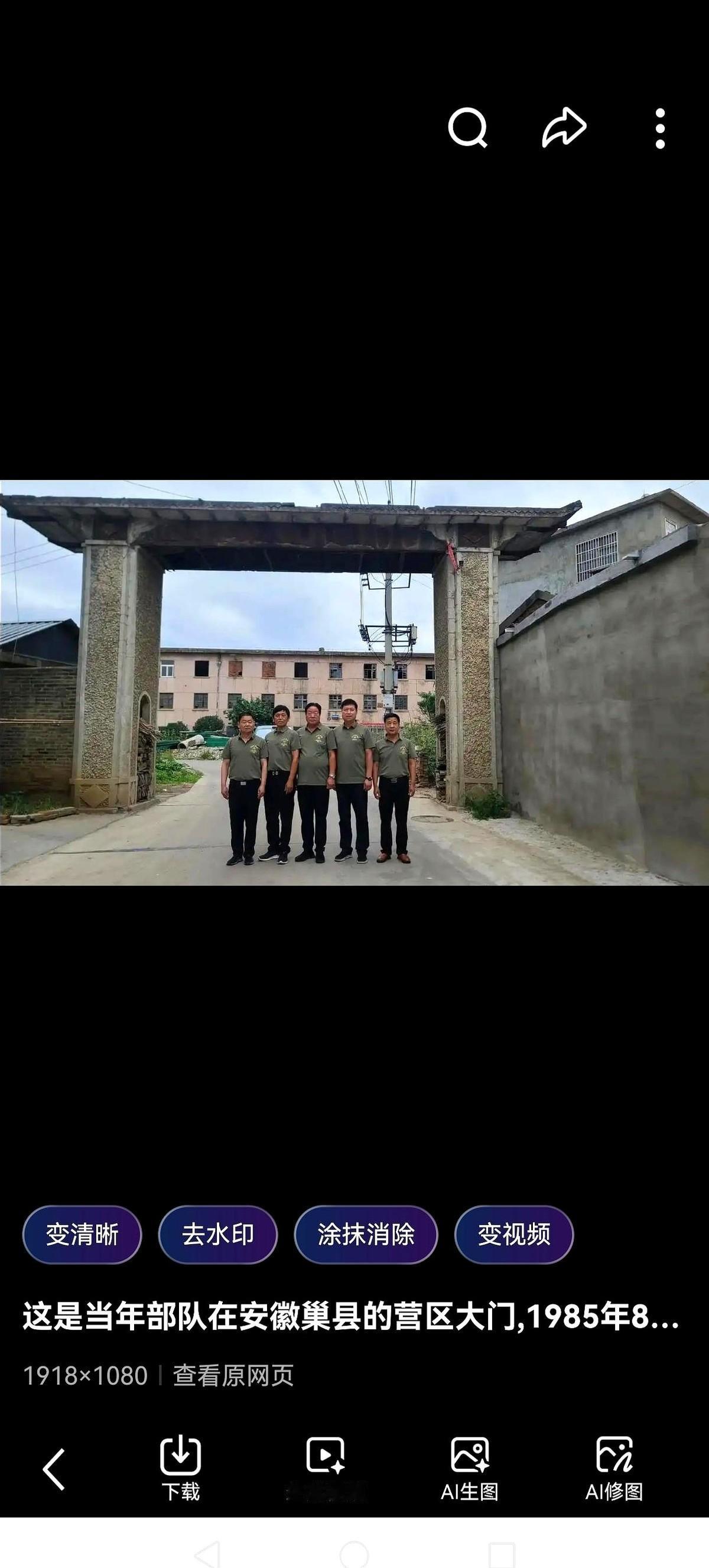1988年那份破译的越军电报,让指挥部空气都凝固了,“三十余名侦察兵被杀,疑似一人所为”。 没人相信这组数字,直到作战地图上39号高地被红笔圈出,一个名字开始在参谋间传:向小平。 这个当时还在军校靶场练枪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即将走进老山的迷雾里。 向小平这辈子跟枪的缘分,是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靶场开始的。 1982年的新兵里,他不算起眼,一米六五的个头在队列里总被前面的人挡住视线。 但每次实弹射击,教员都会盯着他的靶纸,20发子弹198环,枪枪咬着十环中心。 那时战友笑他“枪比女朋友亲”,他只是把枪膛擦得锃亮,说“这玩意儿不骗人,你对它用心,它就给你准头”。 那时候全军都在学张桃芳,上甘岭的冷枪英雄靠一把莫辛纳甘能杀214人。 向小平把张桃芳的“守株待兔”战术写在笔记本第一页,白天练瞄准,晚上就在帐篷里用树枝比划弹道。 56式半自动步枪的后坐力震得肩膀青紫,他就在枪托缠两层棉布,硬是把100米距离的十环命中率练到了90%。 教员后来跟人说:“这小子眼里有准星,心里更有。” 39号高地的丛林能吞掉一切声音。 向小平潜伏的第四天,暴雨冲垮了伪装网,他只能缩在石缝里,嚼野果充饥时听见越军巡逻队的脚步声。 那把79式狙击步枪被他用泥浆裹得严严实实,枪口对着200米外的堑壕入口。 他知道电报里的数字怎么来的,对面的狙击手正用SVD步枪点名,而他的任务,是让那支枪永远哑火。 夜里降温,他把雨衣裹住枪身,自己抱着冰冷的枪管打盹,梦里都是靶场的枪声。 四十天里,他打了31枪。 第17天那个清晨,逆光让堑壕里的机枪手成了剪影,他屏住呼吸,手指轻扣扳机。 子弹穿过瞄准镜十字线时,他看见对方钢盔上的红五星晃了一下,然后栽倒。 后来清理战场,战友数出30具越军尸体,只有一个重伤的俘虏活着,说“每天都有人倒在同一个位置,我们叫那里‘死亡路口’”。 向小平没去看那些尸体,只是把磨平花纹的弹匣拆下来,数着里面剩下的9发子弹,像清点刚领的新装备。 1998年海关缉私队招人,考官看着报名表上“老山神枪手”的备注笑了:“这年代哪用得着开枪?”向小平没说话,只是在模拟抓捕演练里,隔着仓库铁门听出了三个人的脚步声,连谁拿着手铐谁提着电筒都分毫不差。 后来破获粤港走私车案,他蹲守三天,就靠观察货车轮胎的新旧程度,锁定了32辆走私车的藏身处。 队友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指着轮胎印:“跟瞄准一个理,反常的地方就是靶心。” 现在向小平的办公室抽屉里,还锁着两样东西:老山战役时磨穿底的作战靴,鞋头补着块迷彩布;缉私队第一次授奖的证书,边角被水浸得发皱。 去年建军节,有新兵来采访,他翻出作战靴说:“当年在39号高地,我总怕鞋磨破了暴露目标,现在才明白,真正要守住的,从来不是脚下的地,是心里的准星。” 那双补过的靴子摆在桌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鞋面上映出小小的光斑,像靶纸上的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