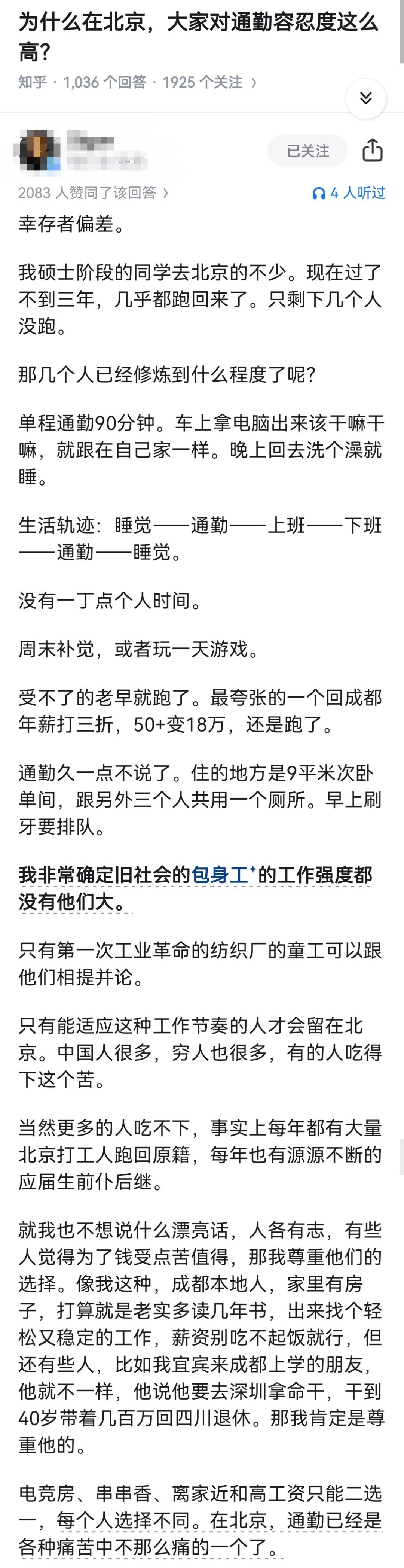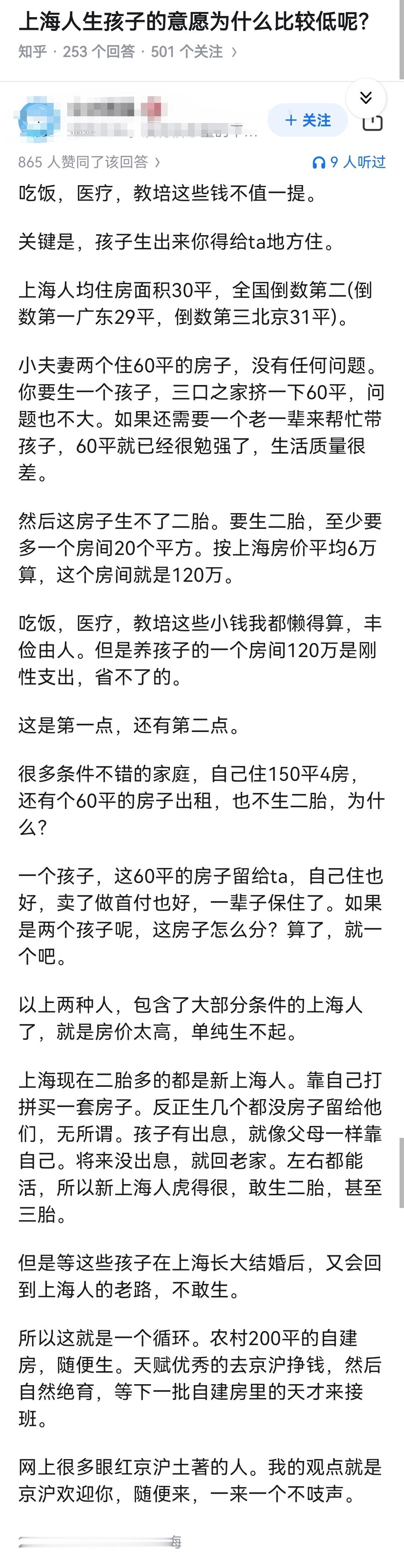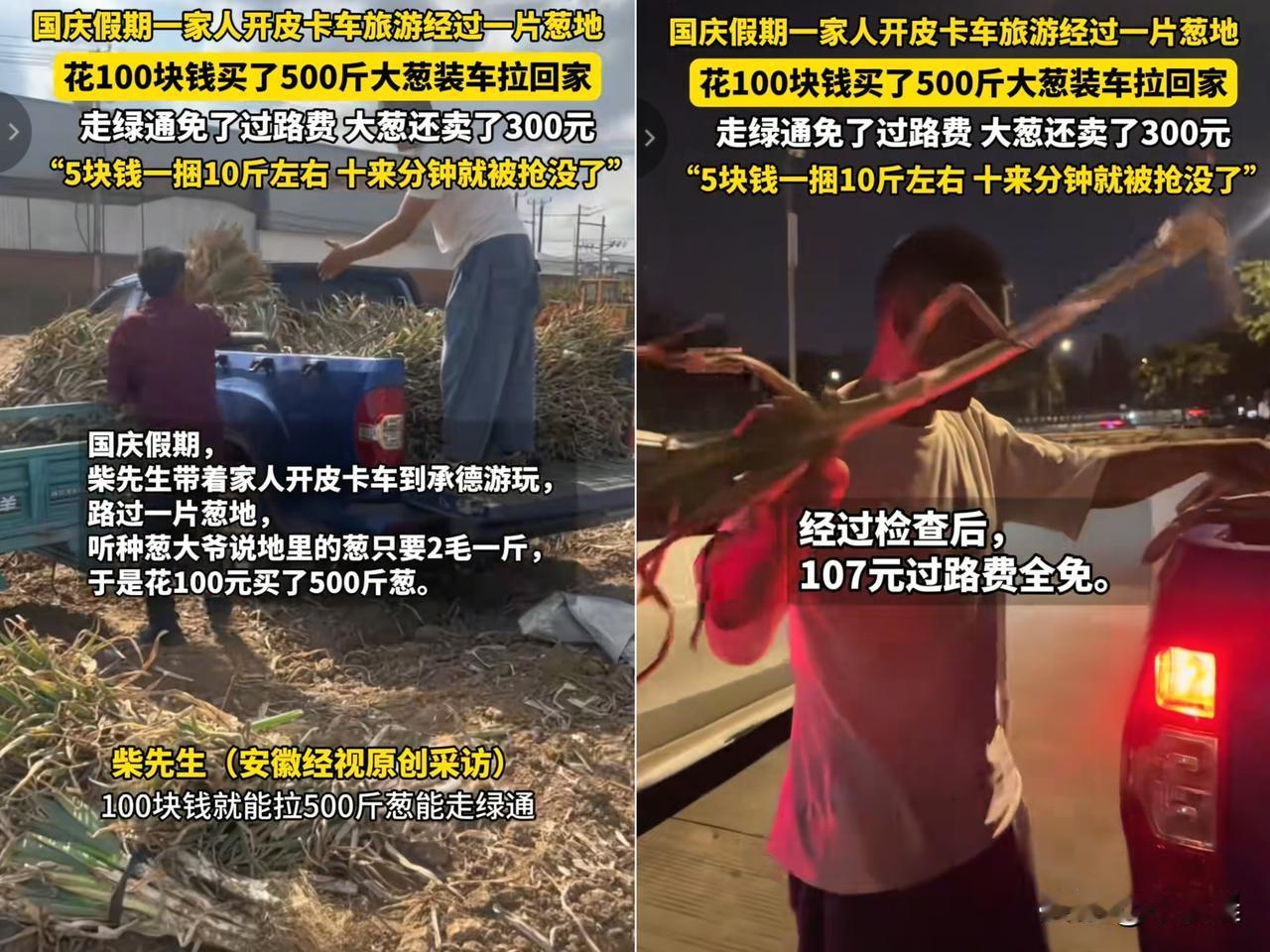北京万佛华侨陵园里,有块刻着话筒的墓碑总亮得晃眼,常年摆着鲜花。这是罗京的墓,去世这么多年,儿子每年都来,母亲却至今以为他在国外主持节目。 罗京母亲老了以后得了老年痴呆,记忆像碎玻璃片,拼不完整。家里人没敢告诉她真相,只说罗京被派去国外做节目了,这谎一撒就是十多年。 有时老太太会突然拉着家里人的手问,“京京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忘了妈了?”家里人就笑着哄她,“他最近忙,等忙完这阵就回来看您”。老太太点点头,眼神却空落落的,像半信半疑。 没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大家都知道,罗京是老太太活下去的念想。要是真相说出口,她那点脆弱的记忆可能就彻底碎了,往后的日子怕是连点颜色都没了。 2008年夏天,奥运的喜悦还没散,罗京家却被乌云罩住了。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去台里上班,胃里却一阵一阵疼,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淋巴癌。 他没告诉任何人,照样播新闻,还偷偷准备奥运火炬传递。作为第140棒火炬手,传递路线就在天安门附近。那天他特意系了条深色腰带,没人知道,那是为了按住腹部的疼痛。 传递时他背挺得笔直,笑着跟路边观众挥手,步伐稳得看不出异样。结束后他先跟工作人员道谢,坐上车才敢用手按住肚子,额头上全是汗。 8月31日是他最后一次播音。那天他提前半小时到岗,花了10分钟逐字核对稿件里的生僻地名,对着镜子反复调整领带。直播时声音平稳有力,跟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每一天一样。 播完最后一条新闻,他仔细叠好稿纸放进文件袋,才跟制片人小声说“接下来想请个假”。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假。 住院后他也没闲着,每天坚持练声,护士进来换药,总能看到他拿着新闻稿在小声朗读。2009年春节,医生特批他回家吃年夜饭,他给儿子罗疏桐包了个特别厚的红包,摸着儿子的头说“要好好读书”。 可到了5月,他的身体越来越差。6月4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他看了一眼床边的儿子,眼睛慢慢闭上了。临走前,他没留遗书,只跟守在旁边的同事说“稿件再核对一遍”。 罗京走后,刘继红整整一年不敢碰电视。新闻片头曲一响,她心口就像被攥住一样疼。有时她会在深夜坐在沙发上发呆,总觉得门会突然被推开,罗京会笑着说“我回来了”。 可门从没开过。她得撑起这个家,白天照顾公婆,晚上辅导儿子功课,还要应付没完没了的媒体电话。有一次她在厨房准备晚饭,突然就站在瓷砖前动不了了,大脑一片空白,就这么发呆了四个小时。 2016年,刘继红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一位做实业的富商。对方知道她的过去,却从不多问,只默默帮她分担家里的事,对罗疏桐也像亲儿子一样。 消息传出去,网上骂声一片。有人说她忘恩负义,有人说她攀高枝,还有人说她不配提罗京。刘继红没回应,她知道,懂她的人自然懂。 罗疏桐比谁都清楚母亲的不易。父亲葬礼上,他全程没哭,攥着拳头说“爸不希望我软弱”。后来有人在网上骂母亲,他没跟人争论,只是默默记在心里,之后每年都会去给父亲扫墓。 他留学美国时,从没跟同学提过自己的父亲是谁。申请奖学金时,材料里只写自己的成绩和实践经历,绝口不提“罗京儿子”的身份。有同学偶然知道后,他也只是淡淡说“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回国找工作,他选了跟媒体无关的行业,从基层做起。公司想借他父亲的名气做宣传,被他拒绝了,“我想靠自己的能力站稳脚跟”。 罗京的墓碑是家里人一起设计的,特意选了不易脏污的石材,上面刻着一支话筒。那话筒的纹路,跟罗京生前常用的那支一模一样,下方还刻着一行小字“声音永存”。 每年清明,刘继红都会亲自来擦墓碑上的话筒,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一件珍宝。罗疏桐会带来父亲生前喜欢的白菊,蹲在墓前跟父亲说说话,说说自己的工作,说说家里的近况。 有人说罗京是“时代眼泪”,可对这个家来说,他从不是过去式。他的声音,他的叮嘱,早就刻进了家人的生活里。刘继红把他的照片收在抽屉最里面,却把他的精神留在了日常里;罗疏桐没活在父亲的光环下,却活成了父亲希望的样子。 其实人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刘继红选择重新开始不是错,罗疏桐坚守纪念也不是执念。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好好活着,也好好怀念。 你们觉得,刘继红改嫁是对是错?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选择?来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