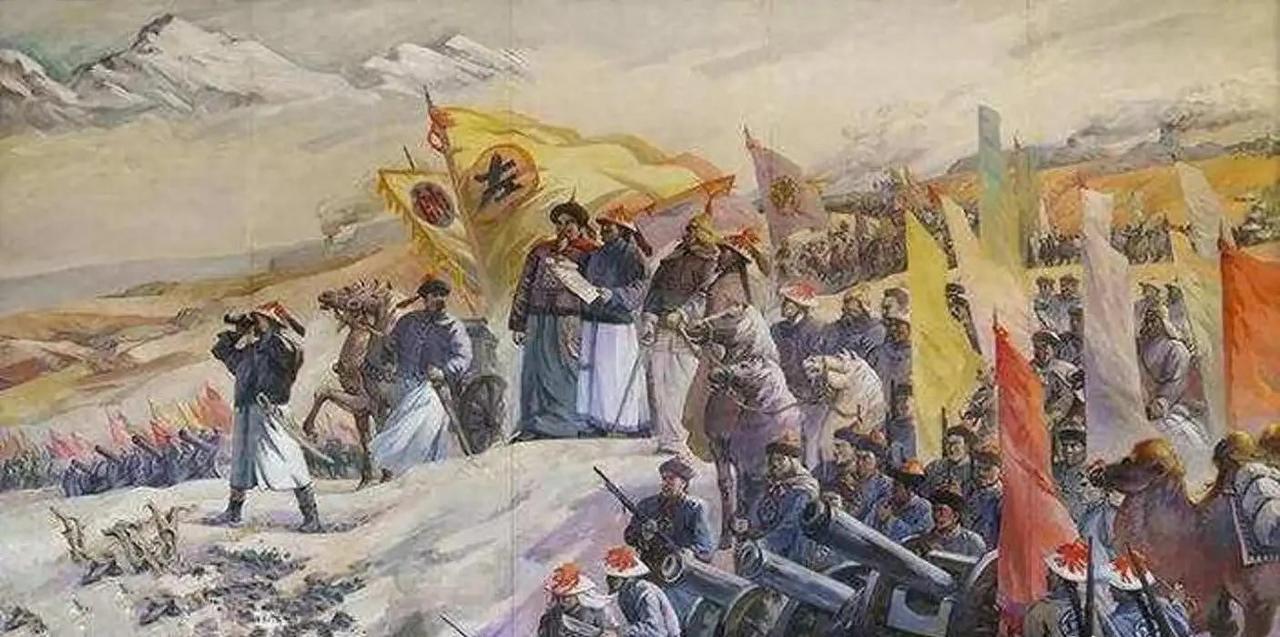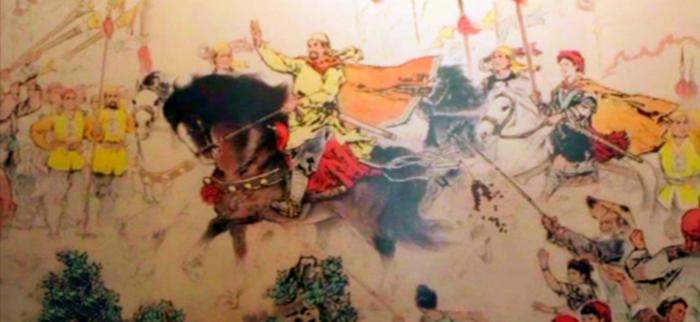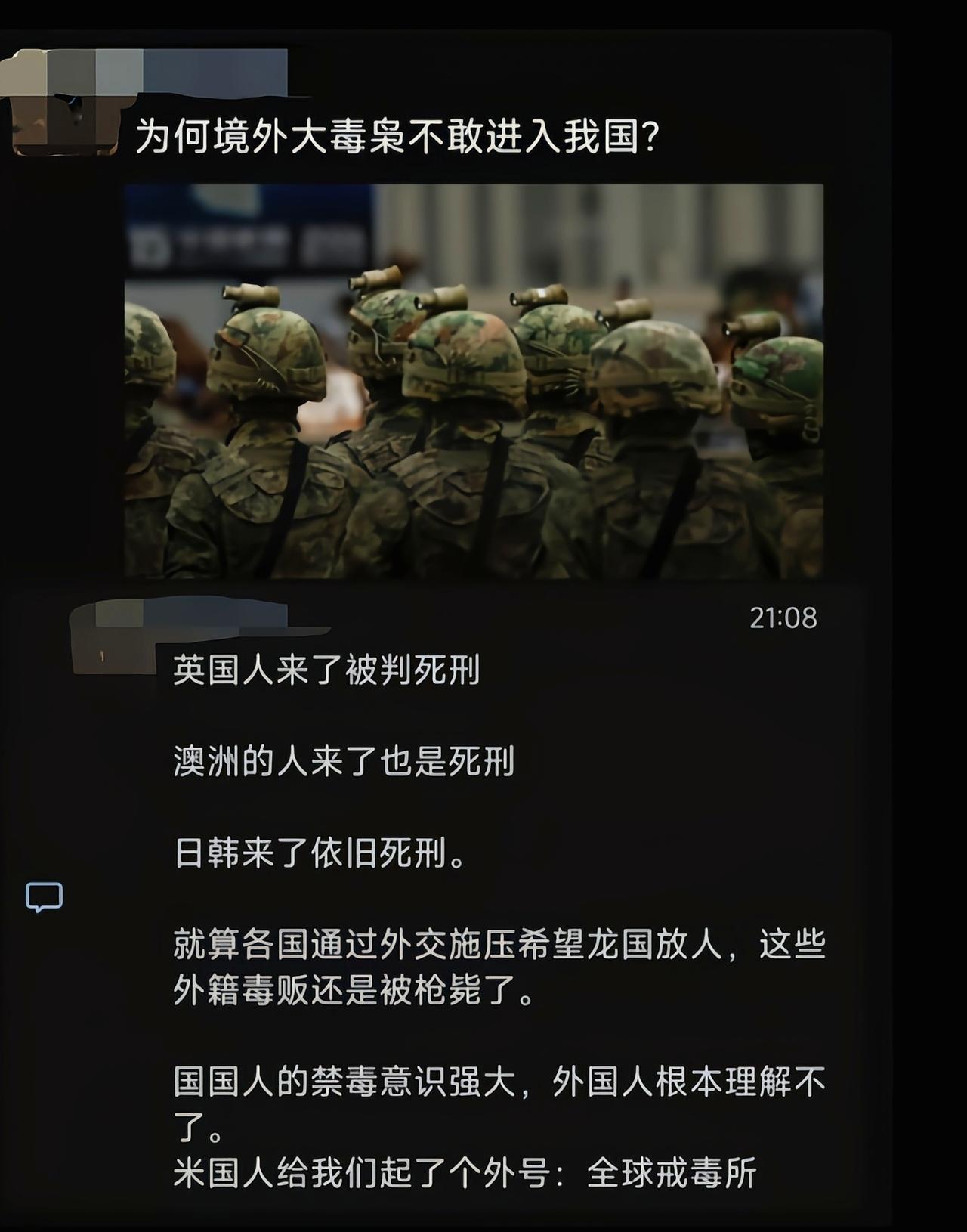1863年那会儿,太平天国的沃王张乐行被自己人出卖,落到了清军手里。这位53岁的老将本来也算是个传奇人物,谁曾想结局竟如此凄惨。更可怕的是,清军统帅僧格林沁竟当着他的面,对他儿子和妻子施以凌迟极刑。 亳州,僧格林沁的骑兵押着一队人犯穿过南城门。 最前面的老者穿着破旧的棉袄,两鬓斑白,眼神却十分坚毅。 他是53岁的“沃王”张乐行,太平天国最善战的捻军领袖。 此刻正走向自己,以及至亲的刑场。 那么,他为何要反? 其实,张乐行的反,是被逼出来的。 他本是安徽亳州城里的粮行老板,开着间“恒顺号”,日子算得上殷实。 可道光末年,官府的苛捐杂税,逼得他不得不反。 地丁银涨了三倍,漕粮要多交两成,连乡下种地的佃户都被逼得卖儿鬻女。 张乐行亲眼见过邻村的张老汉,因为交不起“耗羡银”,被差役按在县衙门口的石墩上,用藤条抽得后背血肉模糊。 “这世道,穷人连活路都没有。” 他关了粮行,把攒下的银钱分给乡亲,又联络了十几号盐贩、马帮,扯起“劫富济贫”的旗号。 他定了三条规矩:“不抢穷人粮,不欺妇女老弱,不碰行商小贩。” 这一来,百姓都愿跟着他。 他劫的是盐商的驼队,分的是地主的存粮,连亳州闹旱灾那年,他还打开自家粮仓,给饿肚子的乡亲熬粥。 1855年,各路捻军在雉河集聚义,推他做了“盟主”。 他骑黑马,插“张”字旗,队伍从几百人涨到几万,连太平天国的陈玉成都慕名而来。 “张盟主,咱们合兵一处,能啃下清妖的骨头!” 洪秀全封他为“沃王”,从此“沃王张乐行”的名号,响彻淮北。 然而,张乐行的败,栽在“自己人”手里。 1863年,僧格林沁带着八旗精锐和蒙古马队,把雉河集围得水泄不通。 清军的火炮昼夜轰鸣,捻军的粮道被切断,营地里开始煮树皮、挖草根。 这时候,张乐行的远房侄子李勤邦找上门。 这小子原是捻军的蓝旗头领,因作战勇猛被张乐行提拔。 李勤邦扑通跪下:“叔,清军许我九品官,咱降了吧。” 张乐行一脚踹开他:“我起兵是为百姓,不是为当官!你忘了当年咱发的誓?” 李勤邦连滚带爬跑了,转头就向僧格林沁献了密报:“张乐行藏在张家沟,带二十个亲信。” 被捕那天,张乐行的亲兵只剩十几个。 他抄起腰刀要拼,却被清军乱矛按在地上。 铁链锁住手腕:“要杀要剐随你们,但别碰我家人!” 可这句话,僧格林沁根本没听进去。 僧格林沁要将张乐行,来震慑百姓。 张乐行被押到法场时,妻子杜金蝉、儿子张喜、张禾已被绑在木桩上。 杜金蝉头发散乱,却挺直腰板:“乐行,咱没怕过!” 张喜才十七岁:“爹,我不怕疼。” 刽子手的刀光闪过,张喜的惨叫撕裂了冬日的寂静。 每割一刀,杜金蝉就喊一句:“乐行,咱没输!” 张禾的叫声渐弱,杜金蝉的喉咙也哑了,最后只剩血沫顺着嘴角往下淌。 张乐行咬着牙,眼神始终坚毅。 家人都死了,僧格林沁狞笑着凑近:“张沃王,现在服软不晚!” 张乐行啐出一口血:“我反的是吸百姓血的贪官,你才是该千刀万剐的!” 刽子手揪住他的头发,把张喜的碎肉塞进他嘴里。 他紧咬牙关,直到气绝,眼睛还瞪着僧格林沁。 张乐行死了,可反抗的火没灭。 他的部将张宗禹、赖文光带着捻军余部,继续在豫皖一带转战。 1865年,他们还在山东曹州斩杀了僧格林沁。 还有个叫张皮绠的少年,父亲和兄长都跟着张乐行走。 张乐行死后,他跟着张宗禹继续打,15岁就砍过清军的旗子。 1868年捻军失败后,他隐姓埋名回涡阳开了粮铺。 可清政府没放过他。 山东巡抚丁宝桢派暗探找到他,从他家搜出一颗太平天国的朝珠。 1873年,张皮绠被凌迟处死,死时才24岁。 而那个出卖张乐行的李勤邦,虽得了九品官,却一辈子抬不起头。 乡邻骂他“狼心狗肺”,连亲戚都躲着他。 没几年,他抑郁而终,坟头连块碑都没人立。 张乐行的故事,是太平天国里最惨烈的注脚。 他不是什么“大英雄”,只是个想让乡亲吃饱饭的粮行老板。 他没读过圣贤书,却懂“官逼民反”的理。 他的死,不是败给了清军的刀,是败给了时代的脏。 脏在贪官的算盘,脏在叛徒的贪婪,脏在“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腐朽。 亳州的老人至今还说:“沃王张乐行,是咱穷人的骨头。” 或许历史不会记住所有细节,但会记住当压迫到极致,总有人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活。 张乐行的没输,他的反抗,成了后来者最亮的灯! 主要信源:(中华网热点新闻——他是死的最惨烈的武将,亲眼看着老婆和儿子被活剐,自己也被凌迟(2)、张乐行 - 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