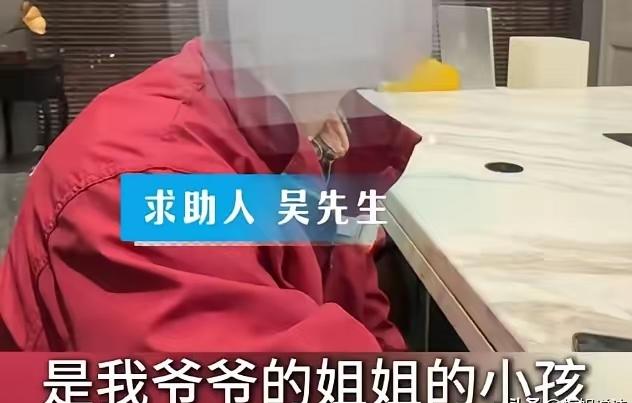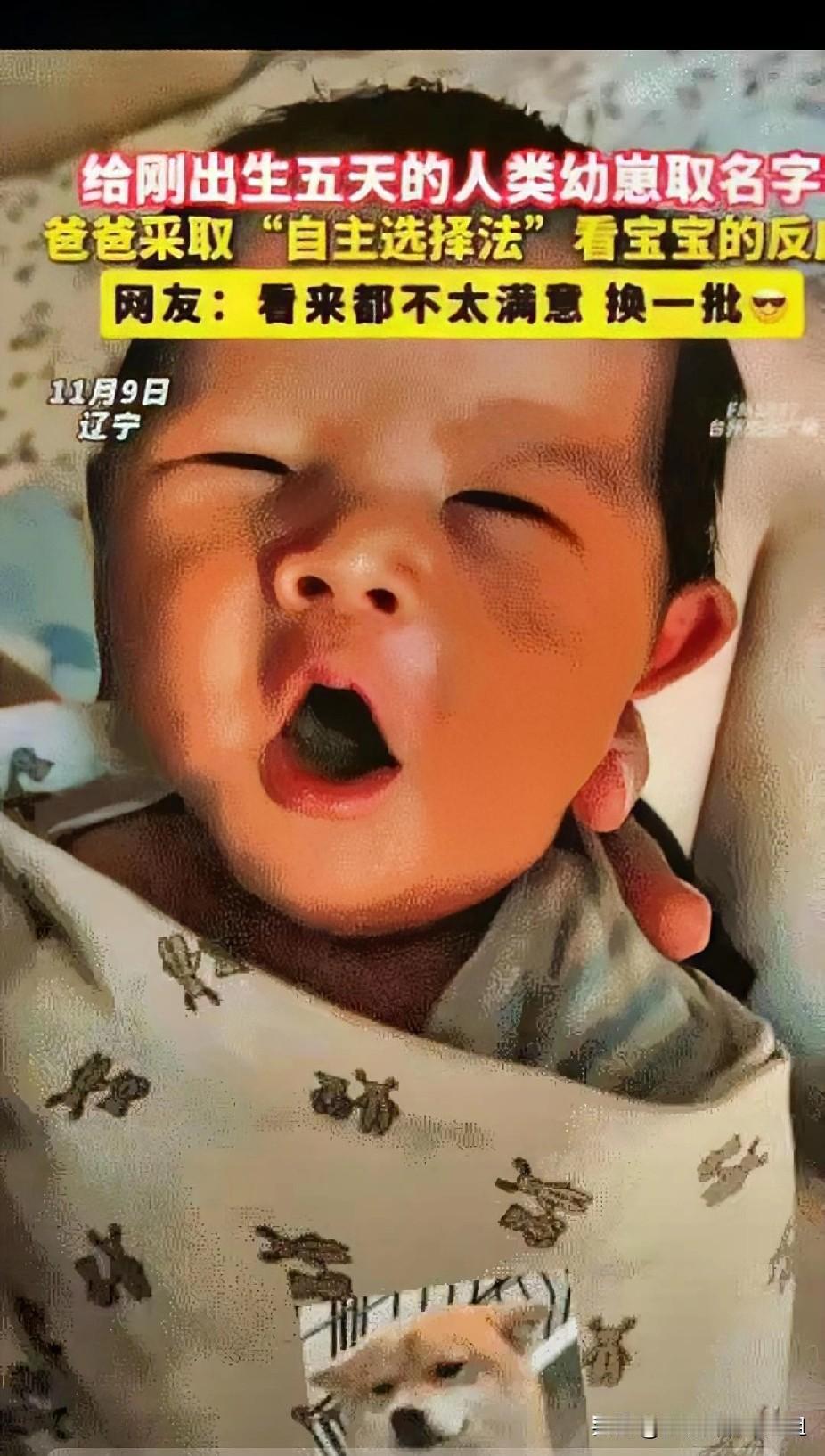太气人了,上医院做手术竟然找不人签字?上海46岁的蒋大姐,平日里安稳度日,偏偏上个月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本想着救人刻不容缓,谁料医院在救治过程中,竟卡在了“找谁签字”这一环节! 蒋大姐的情况颇为特殊:她未婚未育,父母早逝,连亲兄弟姐妹都没有。手术费先是由远房亲戚吴大哥垫付了3万,然而后续21万多的医药费,医院表示必须有监护人签字才能继续治疗。吴大哥跑去居委会寻求帮助,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回复十分干脆:“居委会没有相关权利,我们不能办理。” 您或许会疑惑,居委会作为基层组织,为何连当监护人的资格都没有?实际上,法律早有规定——《民法典》明确,在没有法定监护人的情况下,居委会可以充当这个“家长”。但问题在于,蒋大姐目前只是处于昏迷状态,从法律层面,需要先认定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居委会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监护权。没有这份证明,保险公司不敢理赔,银行不敢支取工资,居委会干着急也没办法。 这看似是个特殊案例,实则戳中了众多独居人士的痛点。如今,不婚不育的年轻人日益增多,谁能保证自己年老时不会生病?要是蒋大姐早做打算,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麻烦。 《民法典》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两种办法:其一为“意定监护”——在您身体康健时,找值得信赖的朋友、居委会甚至邻居,以书面形式明确:“等我失去自理能力,您作为我的监护人,帮我管理财务、照料看病。”这就如同提前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另一个是“遗赠扶养协议”——与愿意照顾您的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对方负责您的生养死葬,您离世后财产归其所有。这样既能有人养老,又无需担忧身后事无人处理。 如今蒋大姐总算脱离了危险,但此事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法律是好法律,可它不会“读心”。您不主动寻求,它又怎知何时该拉您一把? 说实在的,这事儿至少给我三点启示: 第一,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就像开车要系安全带,年轻时花些心思规划监护事宜,年老时便能少受些罪; 第二,若社区想提供帮助,需给予足够“工具”。居委会有心无力,不妨简化认定程序,让他们能更快发挥作用; 第三,独居并非“孤岛”。社会应多伸出援手,让每位老人都能体面生活、安心治病。 您身边有独居的亲戚朋友吗?转发给他们看看,提前准备一个“护身符”,总好过事到临头手足无措!毕竟,谁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信息来源:新闻综合《上海独居女士突发脑溢血,监护困境引关注》《蒋女士监护权争议:法律程序成关键》《蒋女士案启示录:独身社会需未雨绸缪》;上海法制报《无亲属独居者医疗监护难题:法律如何破局?》《民法典视角下的独居者监护权:居委会的角色与限制》《独身人士养老保障:意定监护是关键》《从蒋女士案看独身养老:遗赠扶养协议的应用》《蒋女士案启示录:独身社会需未雨绸缪》《从蒋女士案看独身社会法治保障》2025年11月报道及评论) 脑溢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