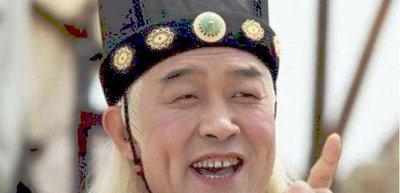1626年,魏忠贤把李成妃幽禁在长春宫,15天不给吃喝,只为将她饿死,可当15天后太监打开宫门准备收尸时,却发现一个女人正坐在镜子前梳头! 太监手中的锡制烛台“哐当”落地,烛火在青砖上滚出半尺长的火星,映着铜镜里那半挽的发髻——青丝如瀑,根根分明,哪有半分饿殍的枯槁? “你是人是鬼?”小太监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手里的收尸白布滑落在脚边。 女人慢慢转过头,铜镜的光恰好落在她脸上,肤色虽有些苍白,却不见半点灰败。“李公公,”她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却异常平静,“15天了,劳你惦记。”正是李成妃。 “鬼啊!”小太监惨叫一声,连滚带爬地冲出长春宫,宫门口的石狮子仿佛都被这凄厉的喊声惊得眯起了眼。 消息像长了翅膀,半个时辰就飞到了魏忠贤耳中。他正把玩着天启帝新赐的一把玉柄匕首,闻言手一抖,匕首“当啷”掉在紫檀木桌上,划出一道深痕。“不可能!”他猛地起身,蟒袍的下摆扫落了桌上的茶盏,茶水在“九千岁”的令牌上洇开一片深色,“张裕妃14天就硬了,眼睛瞪得像铜铃,她凭什么多撑一天还能梳头?” 三年前的那一幕,此刻在魏忠贤脑海里翻涌。张裕妃怀着龙胎,本该是泼天的富贵,却只因没给客氏送礼,还嘟囔了句“奶娘管得太宽”,就被他和客氏联手扣上“假孕欺君”的罪名。 天启帝那时正沉迷于新做的木工模型,听了客氏几句哭诉,头也没抬就挥了挥手:“拖去冷宫,别来烦朕。”结果呢?14天后,冷宫的门一开,张裕妃的尸体已经凉透了,手指还保持着抓挠墙壁的姿势,指甲缝里全是血泥。 有了张裕妃的先例,后宫的妃子们个个噤若寒蝉,连走路都怕踩重了惊着客氏。可偏偏李成妃是个例外——她是怎么敢的? 魏忠贤带着人闯进长春宫时,李成妃刚梳完最后一缕头发,正将桃木梳插回发髻。她转过身,对着魏忠贤盈盈一拜:“九千岁大驾光临,臣妾这长春宫简陋,怕是招待不周。” 魏忠贤的目光像刀子,刮过她的脸,她的手,最后落在铜镜前那半碟蜜饯上——蜜饯是金橘味的,晶莹剔透,显然没放多久。“哪来的吃食?”他咬着牙问。 李成妃没答,只是轻轻抚摸着袖口。那里藏着一块玉佩,是天启帝三年前赏的,羊脂白玉,刻着“平安”二字。魏忠贤认得那块玉,当年天启帝笑着说:“成妃性子直,配这‘平安’正好。”他心里清楚,这块玉就是免死金牌,真要把事闹到天启帝面前,哪怕皇帝再糊涂,也未必会让自己动这块“平安”玉的主人。 “搜!”魏忠贤吼道。太监们翻箱倒柜,床板掀开了,墙壁敲遍了,连房梁上的灰尘都扫了下来。可除了那半碟蜜饯,再没找到半点干粮的影子。 谁能想到,李成妃的生路,藏在那些无人留意的角落? 长春宫东墙第三块地砖是松的,下面空着,能容下十数包用油纸裹好的干馒头;屋檐下的燕窝被掏空了半只,里面灌着熬得浓稠的蜂蜜膏,用蜡封了口,鸟雀都啄不开;院子里的老海棠树,树干离地三尺有个指节宽的洞,里面塞着两罐腌菜和一小陶壶水,洞口用湿泥混着树皮糊上,远看就像个普通的树瘤。 这些,都是她听了张裕妃的死讯后,悄悄准备的。她知道,客氏和魏忠贤的刀,迟早会落到自己头上——毕竟,她前几日才替失宠的范慧妃说了句话。 那日她给天启帝侍寝,见皇帝心情好,便轻声提了句:“范姐姐近来身子弱,宫里的小厨房总给冷饭,怕是不妥。”这话转天就传到了客氏耳朵里,客氏当时就摔了茶碗:“小蹄子敢管老娘的事,看老娘怎么收拾她!” 魏忠贤看着眼前气定神闲的李成妃,突然明白了——这女人不是不怕死,是早就想好了怎么活。 最终,他只能捏着鼻子认栽,对外宣称“查无实据”,把李成妃贬为宫女,打发到西苑守陵。虽没了妃位,却捡回了一条命。 西苑的日子清苦,李成妃却活得安稳。她每日打扫陵寝,种些青菜,偶尔还会对着天启帝的牌位发呆。直到七年后,天启帝驾崩,崇祯帝即位。 新帝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清算魏忠贤。圣旨送到凤阳时,魏忠贤看着那三尺白绫,想起了长春宫那个梳头的女人,最终自缢身亡。客氏更惨,被押到浣衣局,活活打死,尸体扔去喂了狗。 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终于沉冤得雪。李成妃也被召回紫禁城,恢复了妃位。站在熟悉的长春宫前,她摸了摸东墙那块地砖,早已被新砖替换,可她知道,有些缝隙,永远留在了那里。 紫禁城的红墙高十丈,厚三尺,却挡不住人心的算计,也关不住求生的智慧。再黑暗的时代,总有人能在砖石的缝隙里,找到那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