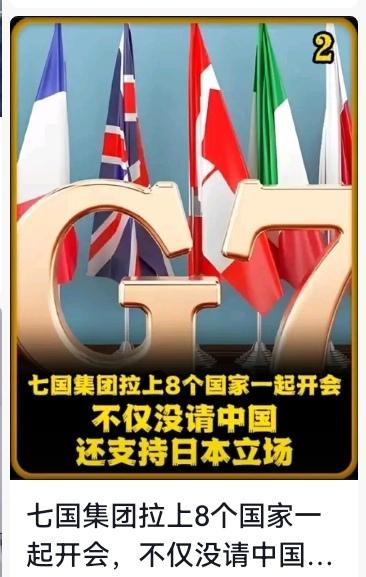以前美国没有给越南实行高关税的时候。越南的工人可傲娇,反正动不动要罢工,各种要求中资企业加薪。不过没想到,这才不过只有几天而已,越南工人的傲娇劲就没了。要是再傲娇,饭碗就没了。 2025年初的越南制造业园区还透着股热闹劲儿,中资工厂的工人脸上满是底气。那时候美国还没对越南加征关税,东南亚这条供应链正是红火的时候,工人们手里攥着选择权,腰杆自然硬气。 胡志明市郊外的电子代工厂里,工人们隔三差五就会因为薪资问题停工半天,要求把时薪从4.5美元涨到5.2美元。成衣车间的女工们更直接,集体提交联名信,提出要增加高温补贴和带薪年假,否则就影响订单交付进度。 那时候的工厂主们也没办法,订单排到了三个月后,客户催单催得紧,只能一次次和工人协商妥协。有个做手机配件的中资老板私下吐槽,光是2024年下半年,车间就因为各种诉求停了五次工,每次都得额外多花十几万美元安抚工人情绪。 工人们的傲娇不是没有道理,当时越南制造业岗位缺口达120万,尤其是有技术的流水线工人,跳槽到隔壁工厂就能涨薪20%。家在平阳省的阮氏梅当时就在两家鞋厂之间挑挑拣拣,哪家给的宿舍条件好就去哪家,根本不愁找不到活干。 可谁也没想到,3月中旬美国突然宣布对越南电子、纺织等产品加征15%的关税,理由是越南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这个政策像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水面,越南出口企业的订单量瞬间断崖式下跌。 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南部工业区的中资企业,某大型服装代工厂原本接到的美国品牌秋冬订单直接被砍了40%,仓库里堆着几十万件待发货的牛仔裤,客户却迟迟不确认提货时间。紧接着,电子厂的生产线也开始减产,原本三班倒的车间改成了两班制,部分工位直接停摆。 订单少了,企业自然要控制成本。先是取消了夜间加班补贴,接着又暂缓了年初承诺的薪资调整计划。更让工人们心慌的是,园区里开始出现裁员消息,有家做玩具出口的工厂一下子裁了150人,门口贴的解雇名单让路过的工人都忍不住驻足观望。 阮氏梅所在的鞋厂也受到了影响,原本满负荷运转的八条生产线停了三条,她和工友们被通知每周只能上四天班,工资按实际出勤天数结算。这个时候的工人们,再也不提加薪的事儿了,反而天天追着工头问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生产。 之前带头罢工的几个年轻人也收敛了锋芒,28岁的黎文俊原本是车间里的活跃分子,现在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主动帮着检查机器设备。他私下跟老乡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要是丢了这份工作,再想找这么稳定的活可就难了。 劳动力市场的风向也彻底变了,原本招聘启事贴满园区公告栏,现在换成了一张张裁员通知。4月初,胡志明市一场招聘会来了三千多个求职者,却只招200人,不少工人拿着简历在各个展位前徘徊,连月薪300美元的岗位都要抢着报名。 中资工厂的管理人员发现,最近车间的生产效率反而提高了。之前工人们到点就下班,现在主动申请加班的人排起了长队,甚至有人愿意接受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有个组长说,现在车间里再也没人抱怨工作累,大家都怕自己表现不好被优先裁员。 关税加征后的第十天,园区里的罢工事件一次都没发生过。反而有工人主动找到企业负责人,提出可以降低薪资保住岗位。某电子厂老板透露,已经有二十多个工人提交了自愿降薪申请,希望能和企业共渡难关。 这种转变背后是现实的压力,越南工人的家庭开支大多是刚性的,房租、子女教育、老人医疗每一项都不能少。家住同奈省的陈文勇算了一笔账,要是每个月工资少拿50美元,家里就得削减一半的肉蛋奶开支,孩子的课外辅导班也得停掉。 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某中资贸易公司的越南区经理说,他们正在和美国客户协商分担关税成本,同时也在开拓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但这些都需要时间。在订单恢复之前,只能尽量压缩各项开支,和工人协商弹性工作制。 园区里的餐馆老板也感受到了变化,之前每到饭点车间工人排队吃饭,现在中午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桌客人。卖米粉的老板娘说,最近工人们点餐都只点素粉,很少有人再加个煎蛋了。 从傲娇罢工到担心饭碗,越南工人的态度转变只用了短短半个月。这背后既有全球供应链调整带来的冲击,也反映了依赖单一出口市场的脆弱性。对于工人们来说,稳定的工作比短期的薪资涨幅更重要,毕竟只有保住饭碗,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现在的越南制造业园区,少了几分之前的浮躁,多了几分凝重。工人们上班时更加专注,下班后讨论的话题也从薪资福利变成了哪里还有招聘信息。这场关税风波像一记警钟,让所有人都明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有谁能永远置身事外,稳定的产业链才是大家共同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