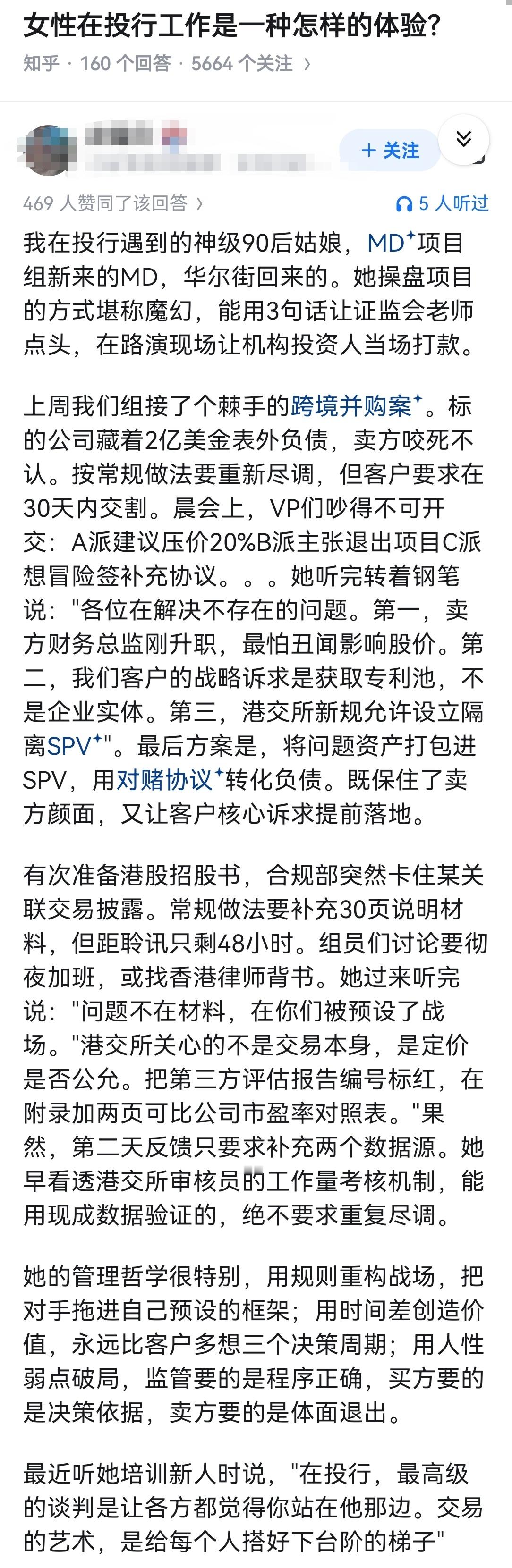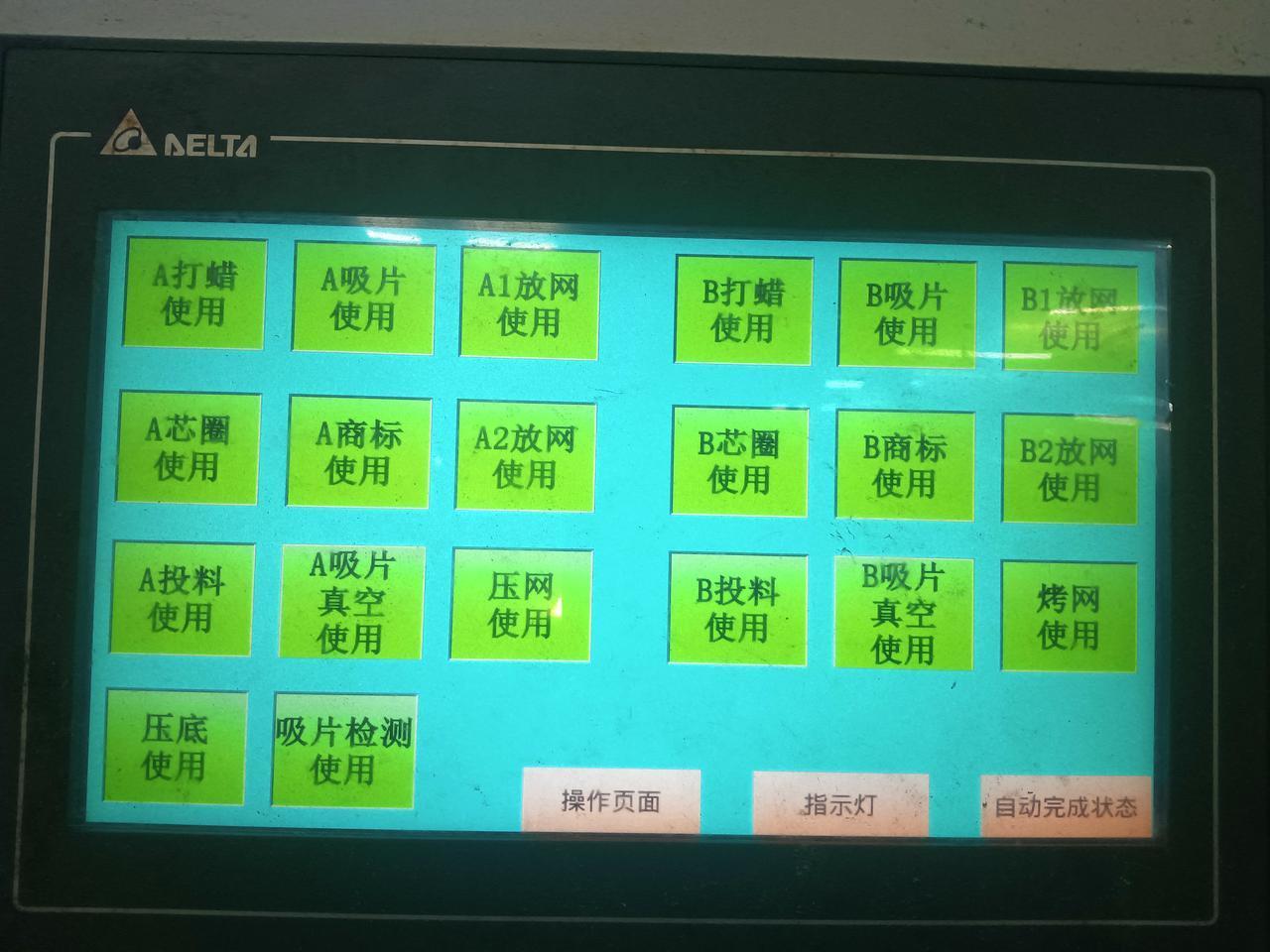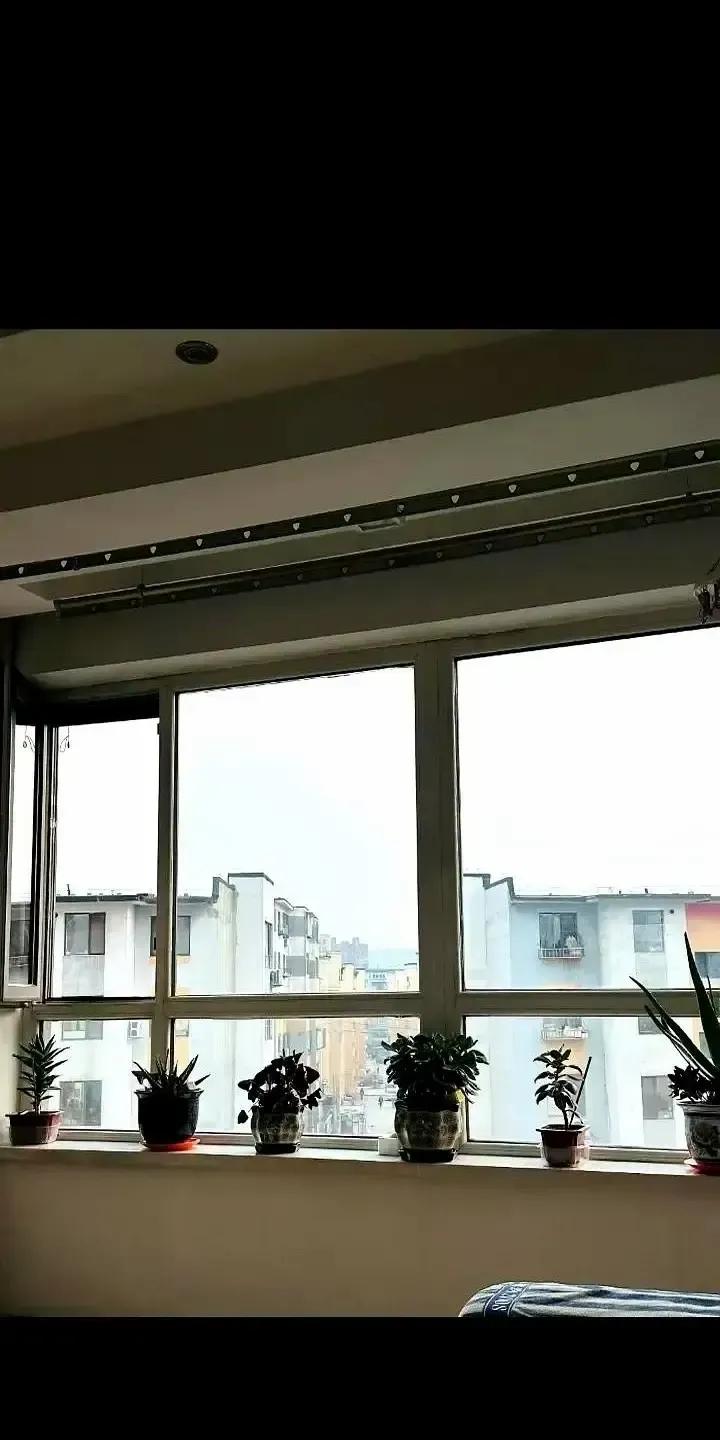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 2000 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中科院院士王贻芳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 30 年。” 杨振宁却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 2000 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这场争论很快传到了科研圈和公众视野,相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会,邀请了物理界、教育界的专家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王贻芳在会上详细阐述了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的必要性,他说,当前基础物理研究处于瓶颈期,很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更高能量的对撞机提供数据。 会议室的空调发出轻微的嗡鸣,杨振宁面前的玻璃杯里,茶叶沉在杯底,像他此刻的语气——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 王贻芳坐在对面,西装袖口沾了点粉笔灰,那是早上给学生上课留下的痕迹,他手里的蓝色文件夹边缘已经磨白,里面是对撞机项目的可行性报告。 2000亿,这个数字在会议室里像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头:是投向地下几十米的粒子隧道,还是铺进千万间教室的课桌椅? 上午九点,研讨会的门被推开时,阳光斜斜切过桌面,把两份报告的影子拉得很长。 王贻芳先开口,声音带着点激动:“现在国际上都在抢这个制高点,我们不建,下一个物理突破就跟中国没关系了。” 他翻开文件夹,指着数据图表,手指在“希格斯粒子后续研究”那行字上顿了顿,像是在确认每个数字的分量。 杨振宁轻轻摇头,老花镜滑到鼻尖,他抬手推了推:“2000亿,够让多少乡村学校有实验室?够培养多少年轻教师?” 他的声音不高,却让原本有些嘈杂的会议室静了下来,后排有人悄悄翻开笔记本,笔尖悬在半空。 难道基础物理的突破和基础教育的夯实,真的只能选其一吗? 王贻芳身体前倾,语气急切了些:“这不是选择题,是发展的必然阶段——美国建费米实验室时,也有人说不如把钱用在民生上,但现在呢?他们拿了多少诺贝尔奖?” 杨振宁没接话,只是拿起桌上的水杯,指尖在杯壁上轻轻划了一圈,像是在丈量什么:“我见过太多大项目上马时轰轰烈烈,最后成了‘半截子工程’,不是技术不行,是基础没打牢,人才接不上。” 有人在后排小声议论,说杨振宁是不是老了,不懂前沿物理的烧钱逻辑;可别忘了,他当年推动中国高等研究院建设时,同样顶着“浪费资源”的质疑,只是那时,他坚持的是“该花的钱必须花”。 王贻芳翻到报告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张全球对撞机分布图,红色箭头直指中国版图上的空白,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基础科学领域要不要“坐前排”的问题,现在不投,以后想追都追不上。 杨振宁终于放下水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轻响:“坐前排需要门票,但更需要能坐得住的底气,底气从哪儿来?从课堂里,从实验室里,从每个孩子眼里的光里。” 会议室的钟敲了十一下,阳光移到了墙角,把两人的影子拉得更远了些。 短期结果是会议结束时,桌上的两份报告被一起收进了标着“待议”的文件夹,封皮上没有签名,只有一道浅浅的折痕。 长期影响是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开始讨论“大科学工程”与“普惠性投入”的平衡,有人算过账,2000亿如果平均分到十年基础教育,每年能让两万个乡镇中学配上标准化实验室。 当下可操作的启示是,任何重大决策前,都该问问:这笔钱,能不能让最多的人看到未来的可能? 散会时,杨振宁和王贻芳在门口遇上,没有握手,却都看了一眼对方手里的文件——一份写着“对撞机”,一份夹着“基础教育调研”。 阳光把两人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一道需要慢慢解开的方程,等号左边是当下的需求,右边是未来的答案,而解题的过程,从来都不轻松
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中科院院士王贻芳说:
昱信简单
2025-11-26 03:43:52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