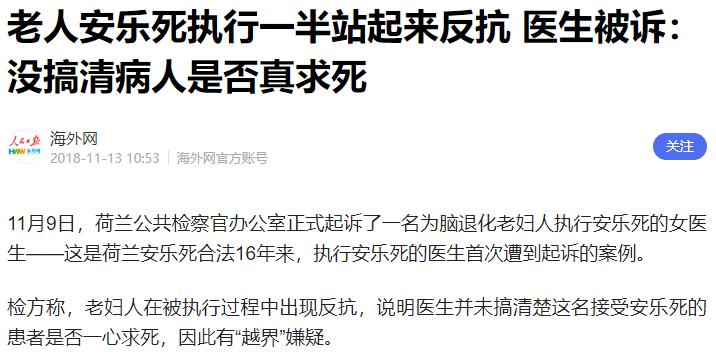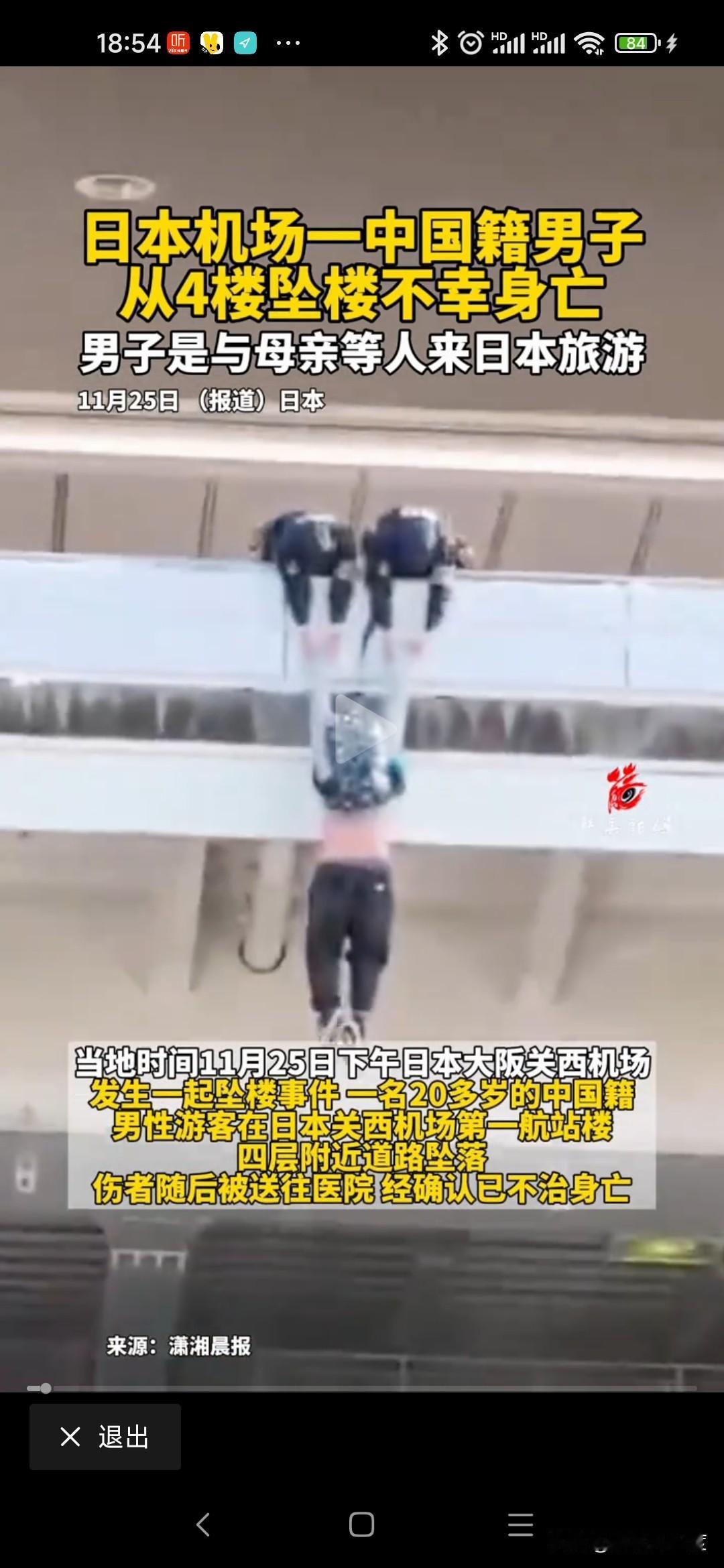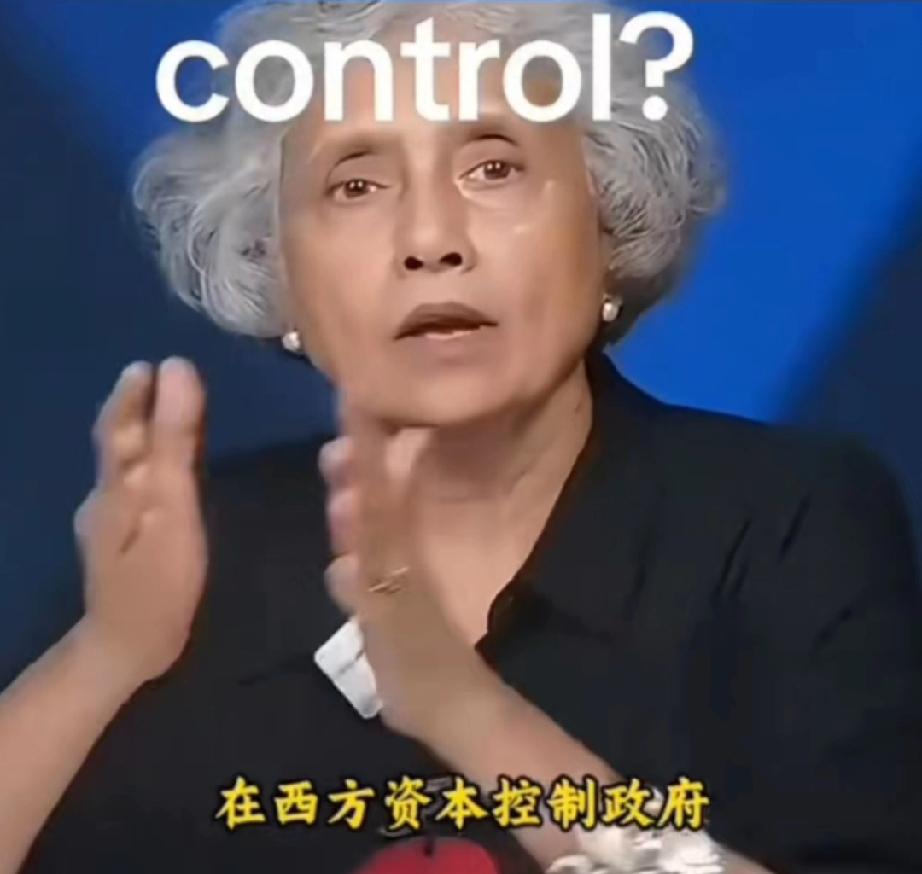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真正允许医生直接结束患者生命的不过7个,新西兰2021年才挤入这个行列。这不是各国政府不近人情,而是安乐死背后藏着的现实残酷远超想象,尤其对穷人而言,所谓的“尊严死亡”更像一道精心包装的陷阱。 瑞士的安乐死机构早就把这生意做成了产业链,“尊严”公司收着每年550元的会员费,“解脱”公司光2017年新增会员就带来300多万固定收入,这些费用还不包含面谈、指定酒店和最终那两杯药的开支。 台湾体育解说傅达仁2018年赴瑞士安乐死花了300万新台币,德国富豪更是被收过140万美金,这些机构明着“看人下菜碟”,普通人连入门资格都没有,更别说那些为医疗费发愁的穷人了。 就算在比利时这种号称免费的国家,2016年安乐死人数就达到2023人,是五年前的两倍,法国穷人因为瑞士太贵,纷纷跨境跑到比利时寻求服务。 可免费的往往更贵,加拿大2021年放宽安乐死条件后,出现了穿着特定服装的“安乐死推销员”,专门盯着医院和养老院里的重病患者。有56岁的肌肉萎缩患者被护士劝说安乐死,拒绝后反被指责“自私”;患先天性脊柱裂的患者表达求生意愿,竟遭医生嘲笑。 这些本该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却因为可能存在的利益关联,变成了死亡的说客,而最先被盯上的,永远是那些缺乏话语权和经济支撑的弱势群体。 荷兰这个最早合法化安乐死的国家,2017年有6586人选择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占全年死亡人数的4%以上,其中还有166名早期痴呆患者。 更令人心惊的是2016年那起脑退化老妇人的案例,74岁的她在注射安乐死药剂到一半时突然站起来反抗,却被医生在家人协助下强行注射完毕。 即便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当患者失去清晰表达意愿的能力时,所谓的“自愿”就成了任人解读的模糊概念。美国俄勒冈州的《尊严死法》实施多年,70%的申请者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中不少人面临的不仅是病痛,还有沉重的养老负担和医疗账单,当“体面离去”被包装成一种解脱,经济压力下的选择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谁也说不清楚。 这些国家的实践早已证明,安乐死一旦放开,监管漏洞就像决堤的洪水。瑞士的协助自杀机构靠着会员费、服务费赚得盆满钵满,荷兰的医生会因为担心被起诉而对执行安乐死越来越谨慎,可即便如此,仍有未经充分确认意愿的案例发生。 对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傅达仁那样的财力去“体面”地死,却可能因为无法承担治疗费用,或在医护人员的诱导下,被迫做出违背本心的选择。 而当生命的终结变成一门生意,当贫困成为被放弃的理由,所谓的“尊严死亡”不过是资本裹着伦理外衣的又一场收割,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宁愿承受争议,也绝不轻易打开这扇潘多拉魔盒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