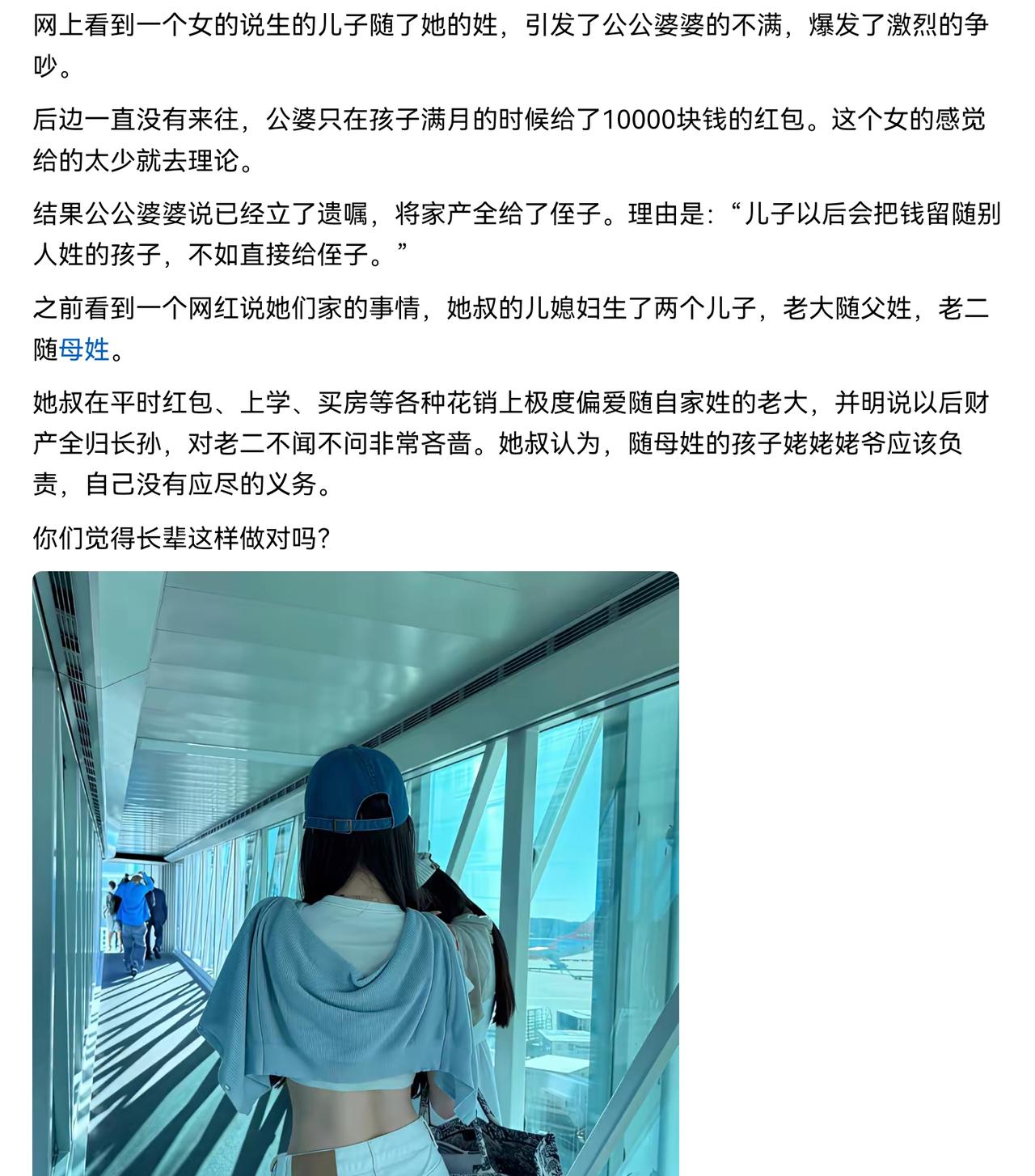1997年,山西平遥人耿保国不顾家人反对,四处借钱凑了100万,买下了3000多平米的明代老宅,为了能住进这个宅子,耿保国花了20年进行内外修缮,为此,他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搭进去了。 那年耿保国四十出头,在平遥古城里开着一家小照相馆,日子过得紧巴巴,却一直对老城里的古建抱着一股执念。他小时候常跟着祖父在城墙根下转悠,听老人讲那些深宅大院的故事,看木雕花窗、砖雕影壁一点点被岁月啃出斑驳。祖父去世前拉着他的手说:“咱平遥的根,不光在城墙,还在这些院里。”这话像颗种子埋在他心里。 97年,他偶然听说城里有座明代老宅要卖,占地三千多平,院落套院落,梁架、斗拱都还是原样,只是荒废多年,屋顶漏、墙体裂,像块蒙尘的古玉。他去看了一眼,站在天井里,阳光从瓦缝漏下来,照在青石板上,他当场就下了决心——要买下来。 家人一听炸了锅。一百多万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平遥普通工人一年工资也就几千块,这钱能盖好几栋新房,还能余下做生意的本钱。妻子劝他别犯傻,说这老宅修起来是无底洞,弄不好把家底掏空还住不进去。亲戚也来拦,说你又不是搞古建的,凭啥揽这瓷器活?耿保国没多辩解,只一句“这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它烂在我眼皮底下”,然后就四处找人借钱,把积蓄全押上,硬是把宅子买了下来。签合同那天,他兜里只剩几十块钱,连回家的车票都得赊。 买下来只是开头,真正的考验是修。明代宅子的结构复杂,榫卯多,工序讲究,稍有不慎就会伤了原物。他不懂,就从零学,跑图书馆查资料,去省古建筑研究所请教老师傅,还跟着修复队打下手。 头几年最难,没钱雇专业队伍,他就自己带着几个老乡干,白天爬高上低拆瓦补梁,晚上借着灯泡的光研究图纸。木料得找老料,纹路、硬度都得配得上原样,他就一趟趟往乡下跑,收旧房拆下的梁柱,碰上合适的,肩扛手抬运回来。砖雕坏了,他找来本地老工匠,按残片一点点复刻,连影壁上的花草纹路都不许走形。 二十年里,他几乎把所有收入都填进宅子。照相馆的生意顾不上,店面越缩越小,朋友笑他“放着现成的钱不赚,去跟木头石头较劲”。他也累,腰伤、腿伤缠过身,有回从房顶摔下来,躺了半个月还惦记着没修完的檐廊。 可每当看到一根歪斜的柱子被扶正、一块残破的砖雕重现花纹,他心里那股热乎劲就又把疲惫压下去。修宅子不光是体力活,更是心力的熬炼——他得在保留原貌和保护安全之间反复权衡,比如有些木构腐朽严重,全留会塌,全换又失了古味,他就琢磨出局部替换、隐蔽加固的法子,让新旧衔接得不露痕迹。 这过程里,家人的态度也慢慢变了。起初埋怨的妻子,看着丈夫灰头土脸却眼睛发亮地忙活,开始帮他递工具、做饭送水;儿子原本在外打工,后来也回来跟着学手艺,父子俩一个测水平、一个刨木料,配合得越来越默契。邻居们从看热闹到佩服,有的还把自己的老物件送来,让耿保国帮忙修整。这座宅子在他们的参与里,不只是耿保国的梦,也成了街坊邻里共同守护的老记忆。 为什么他愿意搭进大半辈子?除了童年的情结,更因为他看清了一个现实——平遥古城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靠的不只是城墙城门,更是这些深宅大院串起来的生活肌理。老宅没人修,就会塌成废墟,后人连模样都看不见。他修的不是一栋房子,是一段能被触摸的历史。修缮的每一步都在跟时间抢东西,今天不动手,明天可能就再也找不回原来的形制、工艺。这种紧迫感让他停不下来。 二十年过去,宅子终于恢复了昔日的气度。走进去,能看见规整的四合院套着跨院,木构梁架沉稳,砖雕影壁细腻,连门槛上的车辙印都被保留下来。它不再是危房,而成为展示平遥明代民居的活标本。有人出高价想买,耿保国摇头,说这宅子卖不得,它是平遥的魂,也是他跟祖先的一个交代。对他而言,住进宅子不是终点,是让这处老建筑重新“活”在当下,让更多人看见古人的营造智慧和生活的温度。 这故事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有多大的财力或本事,是那份明知艰难却不肯退的坚持。在快速变化的年代,很多人选择把老东西拆了建新的,他却反着来,用半生光阴去延续一段快要消失的记忆。修缮的过程充满琐碎、伤痛甚至质疑,可正因为这些真实的摩擦,才显出坚守的分量。一座老宅的重生,靠的不只是钱和技术,更是一个普通人对家乡文化的敬畏和担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