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德国商人在海里捞出7万件唐朝文物,我国想出钱买回,他却开出3亿天价,就在我国犹豫之时,这个德国人竟收了3200万美金,就把所有文物打包卖给了新加坡。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2017年春天的一个午后,上海博物馆的会议室里,窗外的梧桐树刚抽出新芽。 几位研究员围坐在长桌旁,传看着一本从新加坡寄来的厚厚展陈方案。 彩页在手中沙沙作响,当翻到一只青瓷碗的特写照片时,白发苍苍的陶瓷部主任扶了扶眼镜。 照片旁的标注写着“黑石号出水,9世纪”,他指着碗底釉下那抹飞鸟的笔触,声音很轻: “这笔法,典型的唐代长沙窑,没想到在海底泡了千年,彩绘还这么鲜亮。” 这本蓝色封面的方案,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段尘封近二十年的往事,关于一艘沉船,和它载着的六万多件漂洋过海的瓷器。 把时间拨回1998年。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的海域,在赤道的阳光下蓝得晃眼。 德国商人沃特法站在租来的旧渔船上,船舷被晒得发烫。 这个原本在德国经营水泥厂的中年人,皮肤已被海风刮得黝黑粗糙。 他听信了当地渔民代代相传的“海底宝藏”故事,变卖家产,带着潜水装备来到这里,像个孤独的赌徒。 之前两年的搜寻耗光了他的积蓄,合伙人纷纷离开。 直到那个闷热的午后,潜水员在水下二十多米处,用手势比划出一个巨大的轮廓——一块黑色礁石旁,沉睡着一艘古船的骨架。 真正的打捞工作,比想象中艰难百倍。 海底能见度很低,暗流像看不见的手拉扯着潜水员。 他们每天只能在水下工作短短两小时,还要提防游弋的鲨鱼。 最初捞上来的只是一些裹满石灰质硬壳的碎片,沃特法的心沉到了海底。 但转机出现在清理船舱时——潜水灯照进去的刹那,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数以万计的碗、盘、壶、罐,像士兵列阵般整齐地码放着,层与层之间还垫着早已钙化的稻草。 在船舱更深处,防水的油布包裹里,金杯和银壶历经千年海水侵蚀,依然闪着幽暗的光。 最具震撼性的发现出现在第九个月: 一面直径约二十厘米的铜镜被打捞上来。 当附着物被小心剔除,镜背精美繁复的龙凤纹饰清晰浮现,边缘一行錾刻的铭文“扬子江心百炼成”,让船上一位懂中文的当地助手失声惊呼。 消息像冲击波一样传遍了全世界的考古界和收藏界。 当照片传真到南京博物院时,一位戴着套袖的老研究员对着手头的线装《太平广记》,手指微微发颤。 书中记载的唐代皇室祭天重器“江心镜”,竟与照片中的器物描述完全吻合,这是史料记载之外的实物首现。 北京方面迅速组织起由文博专家和外事人员组成的团队,但现实的难题一个接一个砸来: 这批文物存放在印尼的保税仓库,从法律文件上看,所有权属于发现者沃特法以及与他签了分成协议的印尼公司。 而沃特法开出的价码是四千万美元,并且态度坚决: “要么全部买走,要么免谈。” 谈判在雅加达潮湿闷热的雨季里拉锯。 中方的代表在计算,当时全国所有重点博物馆一年的文物征集经费总和,也远远填不上这个数字。 而沃特法也在焦灼地等待,他租用的仓库和雇佣的保安,每天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转机出现在2002年,一批来自新加坡“圣淘沙”机构的代表参观了仓库,他们身后,是愿意慷慨解囊的华人侨领。 2005年,当国内的文博界还在为复杂的审批和筹款程序奔波时,一条简讯从新加坡发出: 以三千二百万美元成交,六万七千件唐代文物及那艘残存的船体,将永久落户狮城。 时光流转到2020年深秋,上海博物馆的特展展厅灯光柔和。 168件“黑石号”出水的珍宝,在恒温恒湿的展柜中静默陈列。 那面传奇的江心镜被安置在展厅中央独立展柜,专业的灯光下,千年沉积的铜绿泛出幽深如墨玉的光泽。 展览开幕当天,一位曾参与当年谈判、早已白发苍苍的退休专家,在展柜前驻足许久。 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它们终究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隔着这层玻璃,我好像能听见一千多年前,扬子江上的风声和船工的号子。” 如今,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地下库房里,每一个收纳“黑石号”文物的特制囊匣上,都贴着三重标签: 黑漆打印的出土编号、可扫描查看三维影像的二维码,以及一张中英文双语卡片,上面工整地写着“出土地: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公元9世纪”。 而在勿里洞岛,当年为沃特法驾船的老渔民头发已经花白,他仍会划着那条斑驳的渔船,载着好奇的游客靠近那片熟悉的海域。 当游客问起海底是否还有宝藏时,他会眯着眼望向蔚蓝的海平面,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 “这海底下睡着的故事,比沙滩上的贝壳还多。它们就像树顶熟透的果子,时候到了,自然会掉下来。” 主要信源:(新华网——“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在上海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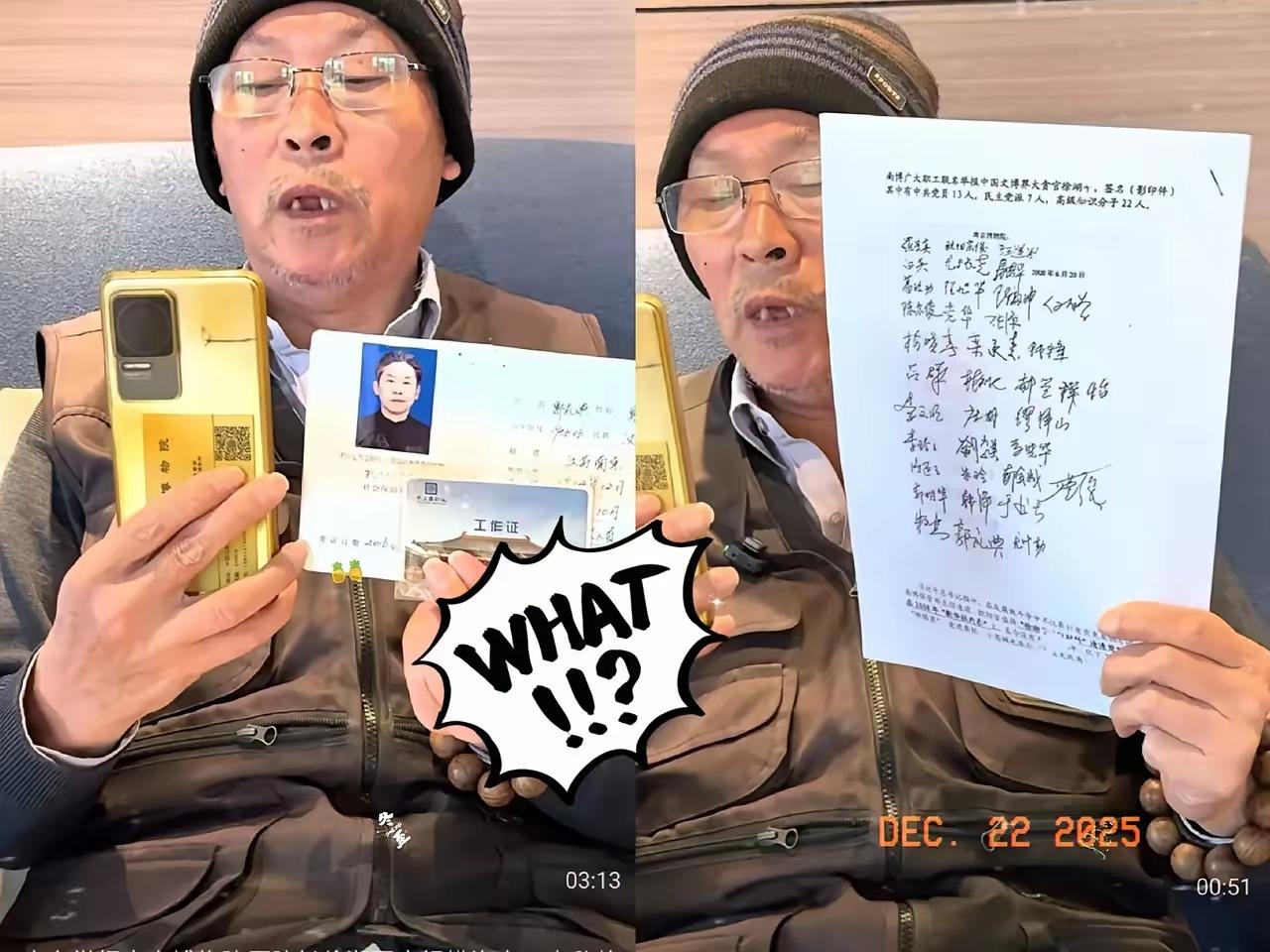





阿超
没回来也好,回来就被借阅了,再过个几年拍卖会上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