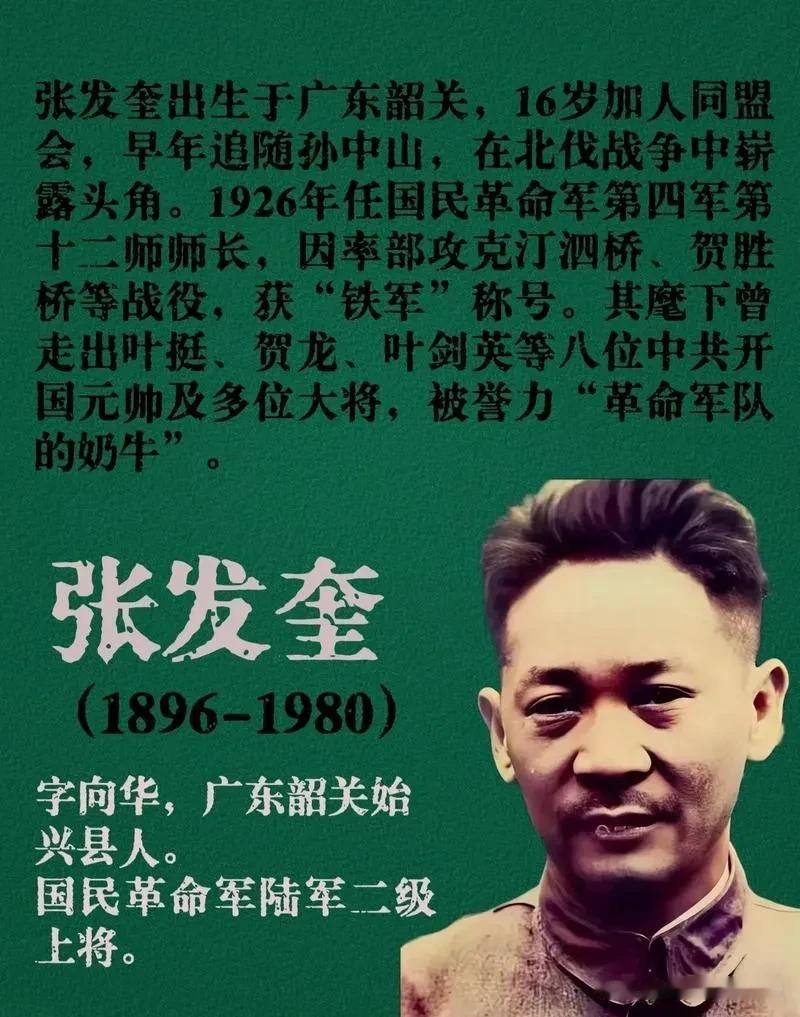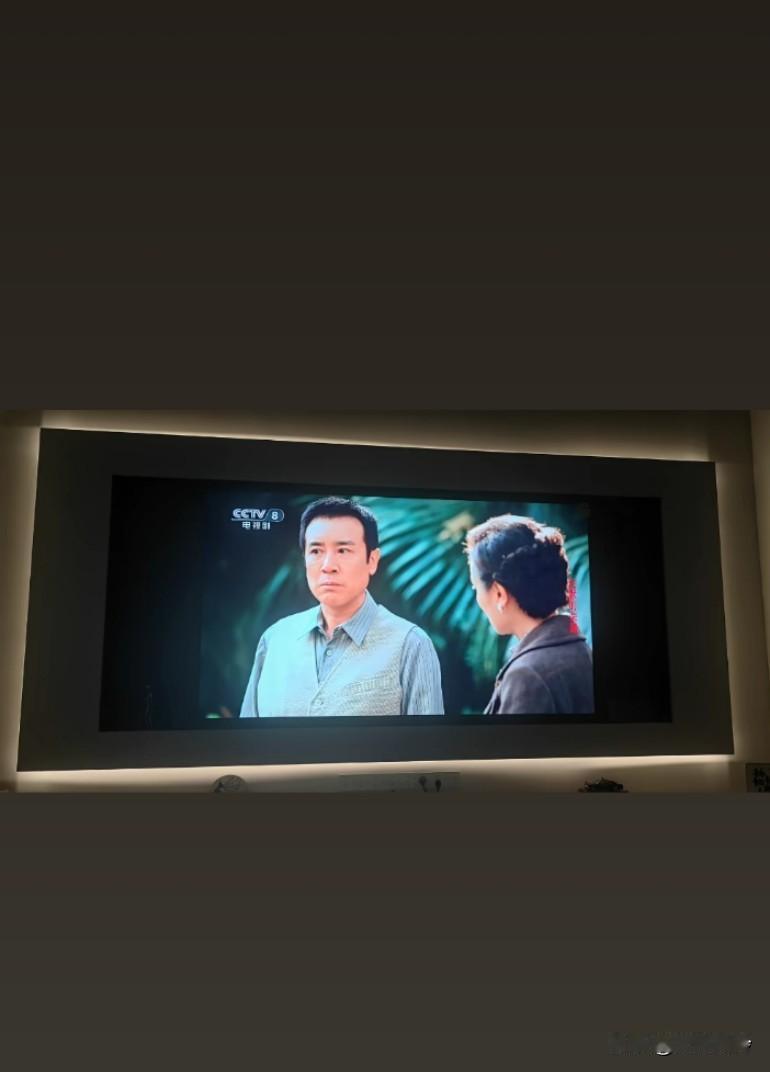1966年3月18日,60岁的罗瑞卿将军从3楼纵身跳下,当场血流不止。消息传出,毛主席、党中央皆震惊不已。 罗瑞卿这个人,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够复杂。 他一辈子绕不过三个关口——一次病得差点死在黑屋子里,一次战场上头部中弹,还有一次,是他自己从三楼跳下去,想结束那场太难的局。 他出生在四川,家境不算太好,地主的壳子还在,可已经撑不起体面。 母亲早走了,父亲也不怎么管事,打牌喝酒,家里乱七八糟。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二十岁不到就离家出走。那时候他读书不多,但清楚自己不想按部就班过完一辈子。 1926年,他到了武汉,考上黄埔军校的分校,算是上了道儿。 后来因为形势变化,学校被打散,他也就成了个没组织的学生兵。 教导团解散那阵子,他人已经病得不行。身上没钱,腿上生疮,肚子也开始拉。朋友看他不行了,带他去了仁济医院。 医院是教会办的,不收白看。 医生说是伤寒,要住院,还得交费。他们两个身上的钱加一块也不够。 讲了好话,又承诺“家里会寄”,医院才勉强收下。 可治了几天病没起色,人开始发烧,眼睛模糊,说话含糊。医院那边也就不耐烦了,直接让人把他抬出去。 他们找了一辆黄包车,把他拖去小旅馆。 旅馆老板一看这人命悬一线,不敢收。 又被拉回医院,医院这回干脆给了车夫点钱,叫他想办法“处理”。车夫也不是坏人,只是实在没办法,绕了一圈,把人送到四川会馆,在后头一间黑屋里放下就走了。 那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地上是块破木板,连被子都没有。 他一个人躺在那儿,浑身发烫,意识模糊。有时候醒一会儿,就觉得天塌了一样,没人知道他在哪儿,也没人会管他。 运气不算太差,会馆里的龛师姓熊,管房子的,年纪不小。 走廊巡查时听见屋里有动静,开门一看,发现了他。熊龛师啥也没说,从那天起,每次自己吃饭时,就多盛一碗米汤,端进去给他喝。 汤淡,米粒少,但是热的,能进肚子。 人是靠那一碗一碗熬过来的。烧慢慢退了,神志也渐渐清醒。 再后来,他竟然能坐起来,最后自己走出那间屋。命是捡回来的。事后他一直惦记这位熊龛师。可等他当了官、想回去找人时,会馆早拆了,旧人踪影全无。 这第一关过了,接下来的路也不轻松。 1931年,江西那边打得正紧,红军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撕得厉害。 罗瑞卿当政委,跟师长一起带队攻打一个叫观音岩的地方。 那地方易守难攻,敌人还占了高地,打起来就是一阵乱枪。他本该在后面盯队伍,可一开火他就往前冲。 敌人机枪扫下来,一颗子弹正好擦着太阳穴打进头里,血当场就冒出来。 战士们抬回救护所,医生看了一眼,说不好办。条件太差,没有设备,也没有药。医生想了个法子,用银元包纱布死死压住动脉。血慢慢止住了,人还在昏迷。 旁边的木工已经开始锯木板准备棺材,有人还笑说这人个子高,棺材得加长。 他其实那会儿有点神志,模模糊糊听见了。心里想,这下完了。可命还是硬,一阵一阵清醒过来。后来做了手术,伤口愈合了,但嘴再也张不开。 说话的时候,像一直在咬牙。 有人说他说话总像压着一口气,他自己笑着回:“咬牙咬习惯了。”别人听了哈哈笑,但都知道,那不是习惯,是留下的疤。 转眼到了五十年代末,他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职务不低,名声也响。 可这位置坐得并不舒服。林掌军,罗瑞卿得跟他对接,两人性格不合,一个沉,一个直。林喜欢绕弯子,罗说话不拐弯。 有些事他不认,不配合,林心里自然不快。 到了1965年年底,他接到通知,说去上海开会。 一落地就被控制了,会议其实是场批判会。叶当众点他,说他“反党””,还说了好几桩莫须有的“阴谋”。 整场会持续几天,他被要求写检查,一次不行写第二次,检查没过就不停会。 那段时间他人很疲惫,有时候连爬楼都费劲,回到房间只能靠在椅子上喘气。写检讨写到凌晨,第二天一早还得坐在台上被批。 1966年3月18日,北京天灰着,风从窗缝钻进来。 他留了一封字条,写给妻子,说没告诉她会议的事是因为“要守纪律”。然后一句话:“永别了。”接着就从三楼跳了下去。 那一跳,本是想断一切。 可没死。落地时人昏了,腿断了,送医抢救,活了下来,左腿伤得太重,最后还是锯了。 从那之后,他被七年,基本与外界断了联系。 直到1973年,林死了,中央开始翻案,他才慢慢被恢复名誉。再出现在公众面前,头发全白了,人也沉静得多。1977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这一生,他没做太多高调的事,也没留下多少名言警句。 可他过的那些关,一关比一关狠。他没喊痛,也没躲。他常说一句:“跟着党走,就不怕路难。”这话他是真信,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他不是完人,也不是什么传奇。他就是个撑下来的兵,一个干了几十年活的人,一个从死里爬出来不止一次、每次都站得稳当的人。 那样的人,在那个年代,不多,但也不算少。 只是他留了个名,让后人还记得,有个叫罗瑞卿的人,三次差点没了命,却始终没有改口,也没有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