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被车裂真不冤?他动的不是蛋糕是别人祖坟 刷到这样一个说法,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好比是现在去印度吼一嗓子: “首陀罗能变婆罗门”,这话听起来扎心却透着精准。 要知道战国时的秦国,跟印度种姓制度是没本质区别的。贵族的爵位土地是世袭的,老子是大夫,儿子生下来就是贵族,哪怕是个草包也能吃香喝辣。而普通士兵在战场上拼断腿,也只能回家种地,永远翻不了身。 商鞅偏要掀了这张桌子。他带着秦孝公给的“尚方宝剑”,立下规矩:不管你是泥腿子还是奴隶,只要在战场上砍一个敌人脑袋,就能升爵位拿土地;砍够五个,还能让家里的奴隶变成自由人。这就相当于告诉秦国底层,你们不用再认命,靠拼命就能往上爬。 可这规矩在老贵族眼里,就是刨他们祖坟。 那些老牌贵族,祖上或许也打过仗立过功,但到了他们这代,早就习惯了躺着享福。商鞅的法令一出来,泥腿子们凭军功就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分他们的土地、占他们的爵位。原本属于自己的特权蛋糕,突然要分给外人,这帮人能不恨得牙痒痒? 有人说商鞅是秦孝公的“打工仔”,其实他是老板手里最锋利的刀。秦孝公要的是强国,要的是秦国能在战国七雄里杀出重围,商鞅的变法正好戳中了他的痛点。老板需要你砍人的时候,你就是功臣;可等老板驾崩,没了靠山,那些被你砍过利益的人,就该反过来砍你了。 商鞅不是没意识到危险。他在秦国推行变法十年,把秦国打造成了虎狼之师,可自己却成了孤家寡人。贵族们恨他入骨,连老百姓也因为变法太严苛而怨声载道。秦孝公一死,太子嬴驷继位,那些憋了十年的旧势力立刻跳出来,罗织罪名诬陷商鞅谋反。 其实大家都清楚,商鞅没谋反。他只是动了太多人的核心利益,这些人需要一个发泄口,需要用最惨烈的方式,来宣告旧时代的回归。车裂之刑,看似是惩罚谋反,实则是旧贵族对改革者的集体报复。 更讽刺的是,商鞅死了,他的变法却被保留了下来。秦惠文王嬴驷杀了商鞅,却继续用商鞅的法令治国,因为他明白,只有这套“狼性规则”,才能让秦国真正强大。说白了,商鞅就是个牺牲品,老板用他的命,换来了秦国的崛起,换来了旧势力的暂时妥协。 后世有人骂商鞅刻薄寡恩,说他死得活该。可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商鞅的孤注一掷,秦国可能早就被其他国家吞并,中国历史或许都会改写。改革从来都是刀尖上跳舞,动别人的奶酪容易,动别人的祖坟难。商鞅敢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哪怕粉身碎骨,也比那些明哲保身的庸人强百倍。 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商鞅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例。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跟商鞅有着惊人的相似命运。王安石想通过青苗法、募役法盘活国家财政,本质上也是在动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这些人原本可以靠兼并土地、逃避徭役坐享其成,王安石的法令一出来,他们不仅要如实交税,还要把手里的粮食拿出来借给农民,自然拼了命地反对。 更要命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比商鞅少了一份“铁腕”。商鞅变法有秦孝公无条件支持,法令推行得雷厉风行,谁反对就办谁;而王安石背后的宋神宗,一会儿支持一会儿动摇,变法派内部还出现分裂,给了旧势力可乘之机。最后王安石两次罢相,变法措施大多被废除,自己也在抑郁中病逝。虽然没像商鞅那样死于非命,但毕生心血付诸东流,何尝不是另一种悲剧? 还有明朝的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各种苛捐杂税合并成一项,按土地多少收税,本质上也是在剥夺官僚地主的特权。张居正活着的时候,靠着万历皇帝的信任和自己的权威,把变法推行得有声有色,明朝财政一度扭亏为盈。可他一死,万历皇帝立刻翻脸,旧势力群起而攻之,不仅抄了他的家,还把他的变法措施全部推翻,张居正差点被鞭尸。 这三位改革家,所处时代不同,变法内容不同,但结局却大同小异。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他们都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些旧势力就像附在国家身上的毒 瘤,改革者要割掉毒 瘤,就必须做好被毒 瘤反噬的准备。 而且他们还有个共同的困境:改革需要依靠皇权,但皇权本身就跟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孝公、宋神宗、万历皇帝,一开始都想通过改革强国,但当改革触及到自己的统治基础时,要么默许旧势力反扑,要么亲自下场清算改革者。老板们要的是“强国”这个结果,至于改革者的死活,从来都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 说到底,商鞅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改革者的宿命。任何触动既得利益的变革,都需要有人付出代价。商鞅用自己的生命,为秦国铺就了统一六国的道路,王安石、张居正用自己的仕途,为后世留下了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这些改革者或许有性格缺陷,或许变法措施有瑕疵,但他们敢于向旧势力亮剑的勇气,值得永远被铭记。毕竟在那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时代,愿意站出来掀桌子的人,从来都不是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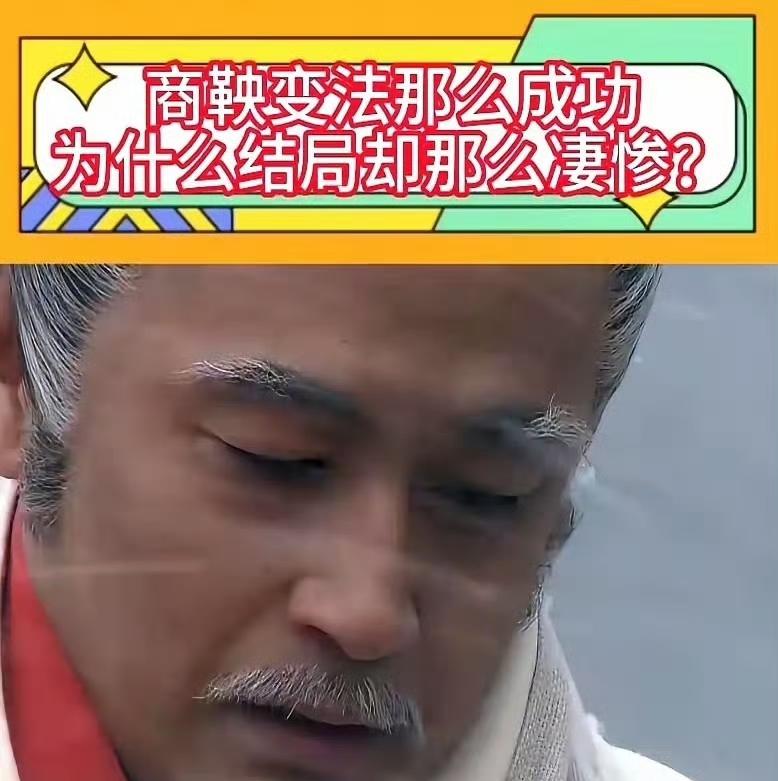

![刘备真要三造大汉成功了,汉朝很可能变成万世一系了[吃瓜]](http://image.uczzd.cn/10736787621719214589.jpg?id=0)







真理就在导弹射程之内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我们历史从不缺仁人志士,以铁血担道义[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