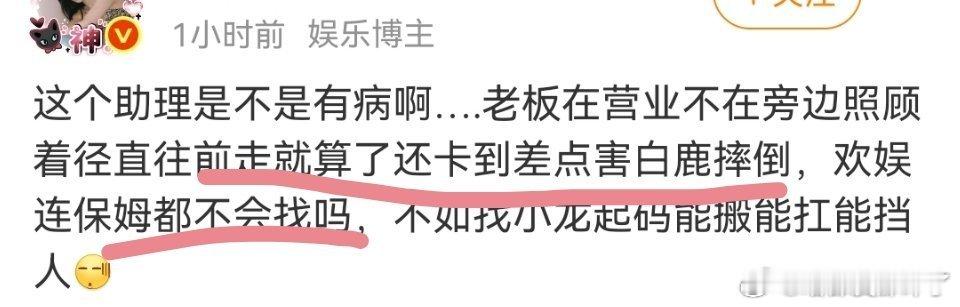我们村有个叫大柱的,在镇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那天下午,我正在他铺子里换轮胎,突然听见里屋传来女人的哭声。大柱正蹲在地上帮我拧螺丝,手上的油污蹭到裤腿上,黑一块灰一块的。他头也没抬,只是往嘴里塞了块口香糖,含糊地说:"别管,是隔壁的王婶。"扳手在他手里转得飞快,轮毂上的锈迹被磨出圈亮边,像嵌了圈银线。 大柱的修理铺在镇口老槐树下,铁皮棚顶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里飘着橡胶和汽油的混合味——我来换后胎,他正蹲在地上跟轮毂较劲,扳手转得咯吱响,锈迹被磨出亮边,像谁在黑铁上镶了圈碎银。 突然里屋传来女人的哭声,细细的,像被捂住嘴,断断续续钻出来。 我手里的矿泉水瓶差点捏扁,“谁啊?” 大柱头没抬,往嘴里塞了块口香糖,甜味混着油污味飘过来,“隔壁王婶,跟她男人吵架呢。” 他手上的动作没停,拧螺丝的力道却松了点,扳手“当啷”掉在地上,滚到我脚边——我看见他耳尖红了,像被太阳晒的,又像不是。 换好胎我没走,蹲在门口假装玩手机,眼睛却瞟着里屋门帘。哭声停了,帘布动了动,露出双沾着泥点的布鞋,鞋头磨破了,露出点白袜子。 大柱突然站起来,“你先回吧,我得去进货。”他推我后背,力气大得像要把我赶走,我却看见他袖口沾着片干枯的艾叶——王婶从来不碰艾草,她闻着过敏。 后来我才知道,哪有什么隔壁王婶——大柱的姐姐嫁到邻村,男人去年车祸没了,她自己又查出病,化疗把头发都掉光了,不敢跟老家父母说,偷偷来投靠弟弟,刚才是疼得忍不住哭。 大柱说,他姐这辈子好强,嫁人的时候风风光光,骑着大柱新买的摩托车,红盖头飘得老远,如今这样,宁愿躲在里屋咬着毛巾哭,也不肯让镇上人看见她掉头发的样子。 他每天收工后去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回来给姐姐熬粥,铺子里那股若有若无的药味,混着汽油和橡胶味,我之前竟以为是机油变质了。 那天我没提钱的事,只是临走时把刚发的奖金塞进他工具箱——后来大柱把钱还给我,硬塞了袋他姐腌的萝卜干,玻璃罐里的萝卜条脆生生的,泡在红辣椒油里,像她当年出嫁时盖头上的流苏。 现在路过修理铺,总看见大柱蹲在地上磨轮毂,锈迹一点点被磨掉,亮边越来越宽,像他藏在油污里的那点温柔,被日子磨得越来越清晰。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是不是都在给生活磨锈迹?把那些难、那些疼,一点点磨成亮边,好让别人看见的时候,只说一句“你看,他过得挺好”。
我们村有个叫大柱的,在镇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那天下午,我正在他铺子里换轮胎,突
昱信简单
2025-12-18 09:50:35
0
阅读: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