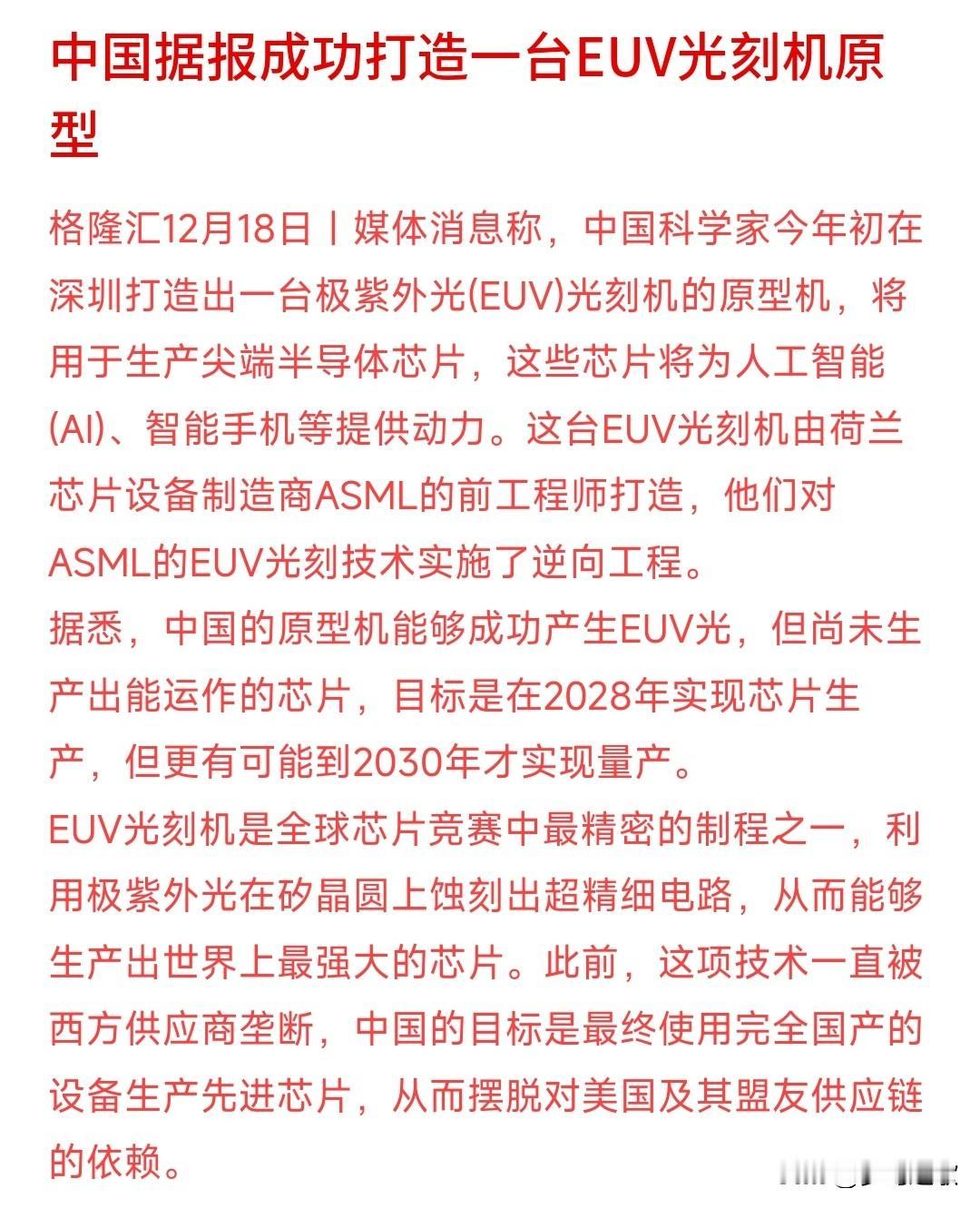“妈妈,外面有人叫你!”八岁的儿子从房间里跑到厨房里告诉我。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了,我正在厨房里洗碗。我擦了擦手,心里犯嘀咕:这么晚了,谁会来叫我?我们刚搬来这个小区半年,认识的邻居不多,亲戚朋友也都住得远,不会这么晚上门。 洗洁精的柠檬味还沾在指缝里,儿子举着奥特曼玩偶冲进厨房时,塑料披风扫过我膝盖——他总这样,跑起来像阵风。 “妈妈!楼下有人喊你!”他仰着汗津津的脸,手里的玩偶举到我下巴,“穿蓝衣服的阿姨,在单元门口晃手机呢!” 墙上的石英钟刚跳过九点十分,我正把最后一只瓷碗放进消毒柜,金属抽屉“咔嗒”一声,在空荡的厨房里格外响。 我们搬来这栋老楼半年,楼梯间的声控灯总在三楼卡住,邻居们的脸大多只在电梯里匆匆闪过,谁会在这时候叫门? 擦手时毛巾蹭到手腕上的银镯子,冰凉的触感让我想起上周六,对门的老太太送了碗绿豆汤,我道谢时她眼神飘着,好像怕打扰。 现在站在防盗门前,透过猫眼往下看——蓝外套,卷发,手里确实举着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 “哪位?”我对着对讲机喊,声音有点发紧。 “是住502的吧?”楼下的声音裹着风传上来,“我是301的林姐,你家阳台的花架是不是松了?刚才晾衣服看见铁架歪在栏杆外,怕半夜刮风掉下去砸到人!” 花架?我忽然想起早上晒被子时,确实觉得最右边的螺丝有点晃,当时急着送儿子去兴趣班,随手把晾衣杆靠在上面就走了。 “啊……是松了,我都忘了!”脸瞬间热起来,对讲机里林姐笑了:“没事,我家有扳手,上来帮你拧拧?你别下来了,楼梯灯暗。” 防盗门打开时,楼道里的声控灯“啪”地亮了,林姐提着工具箱站在台阶上,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翘起来,像只受惊的小雀。 拧螺丝时她的手背上有道浅疤,她说去年帮六楼的独居大爷换灯泡时烫的。“住久了就知道,谁家没点小麻烦?” 她把扳手递给我时,儿子凑过来摸她的卷发,“阿姨,你的头发像棉花糖!”林姐笑得直揉他头顶,“这孩子,嘴比蜜甜。” 原来不是麻烦,是提醒。我总觉得老小区的邻里关系像楼梯间的灰,厚且冷,却忘了上周对门送绿豆汤时,老太太转身前那句“楼道滑,慢点走”;忘了电梯里碰到的小学生,总帮我按住开门键直到我把婴儿车推进去——我们都在等一个主动开口的理由,不是吗? 那晚之后,我开始在电梯里主动问邻居“下班啦?”,儿子会把多余的奥特曼贴纸分给三楼的小学生。 石英钟再指向九点十分时,厨房不再只有消毒柜的咔嗒声,有时是对门送来自家蒸的馒头,有时是林姐喊我下楼拿她女儿穿小的裙子。 儿子的奥特曼玩偶歪在餐桌上,披风上还沾着刚才扫过我膝盖的洗洁精泡沫——原来陌生的楼道里,也藏着会发光的人,只要你愿意先推开那扇没上锁的门。
“妈妈,外面有人叫你!”八岁的儿子从房间里跑到厨房里告诉我。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
昱信简单
2025-12-18 11:50:39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