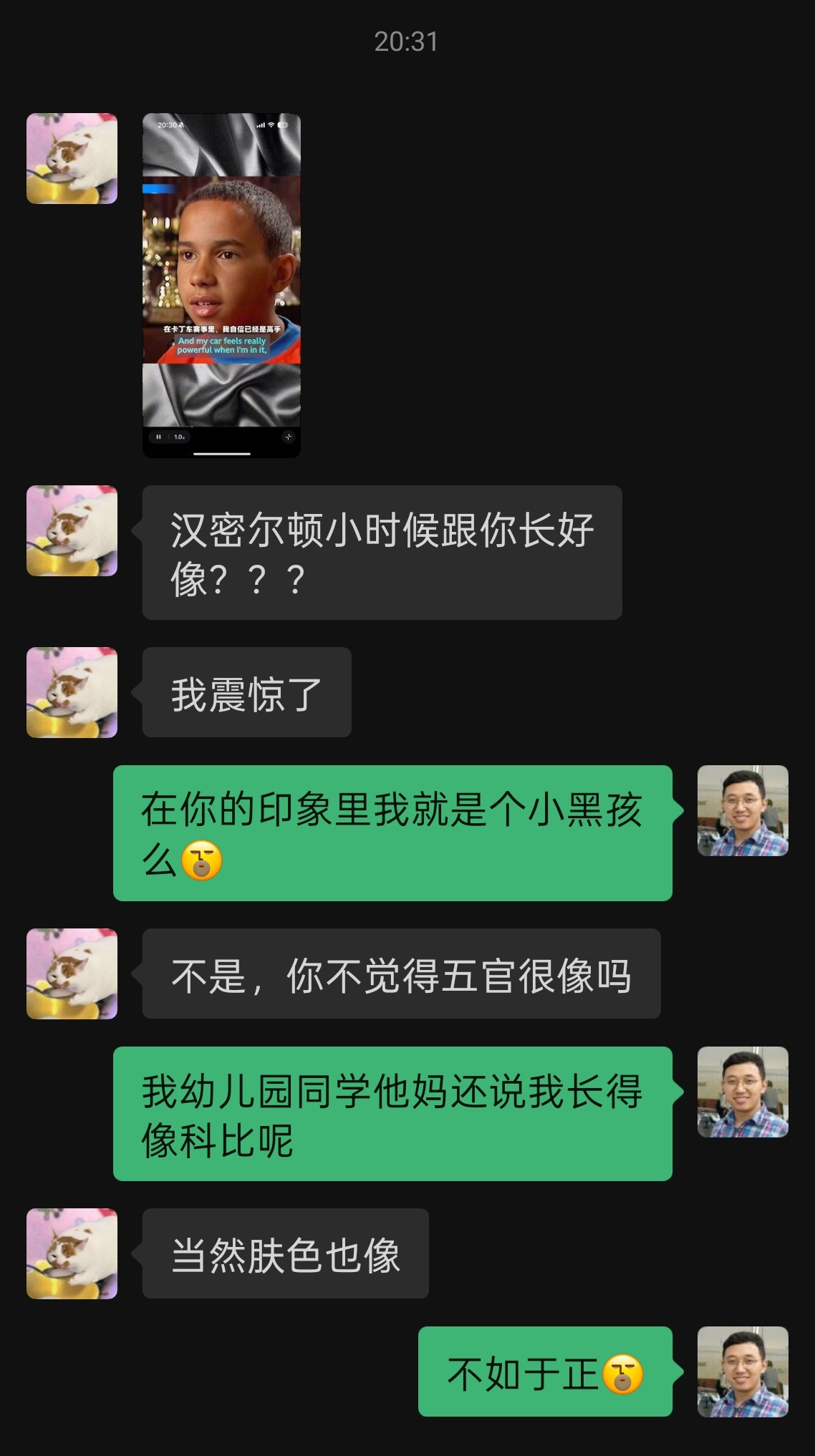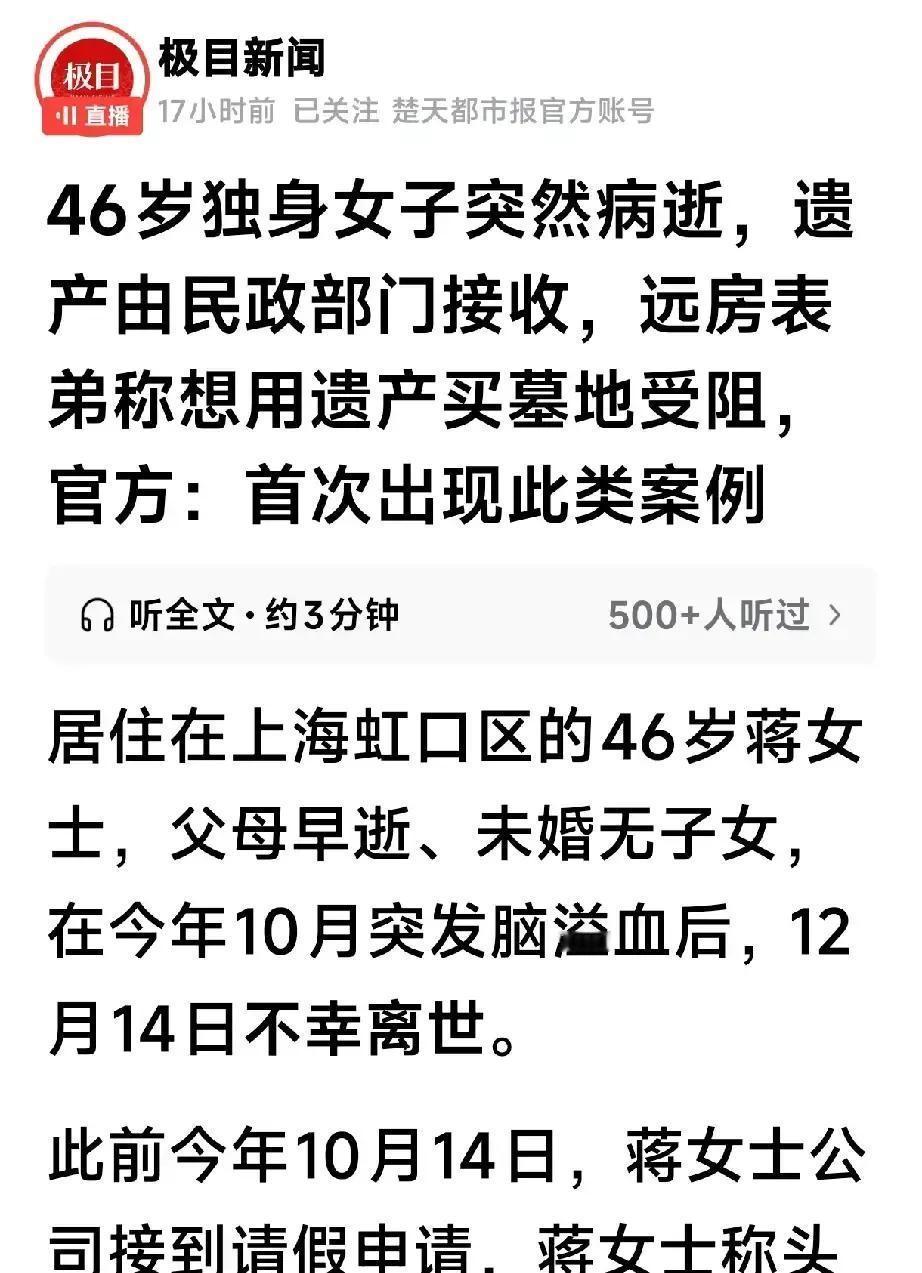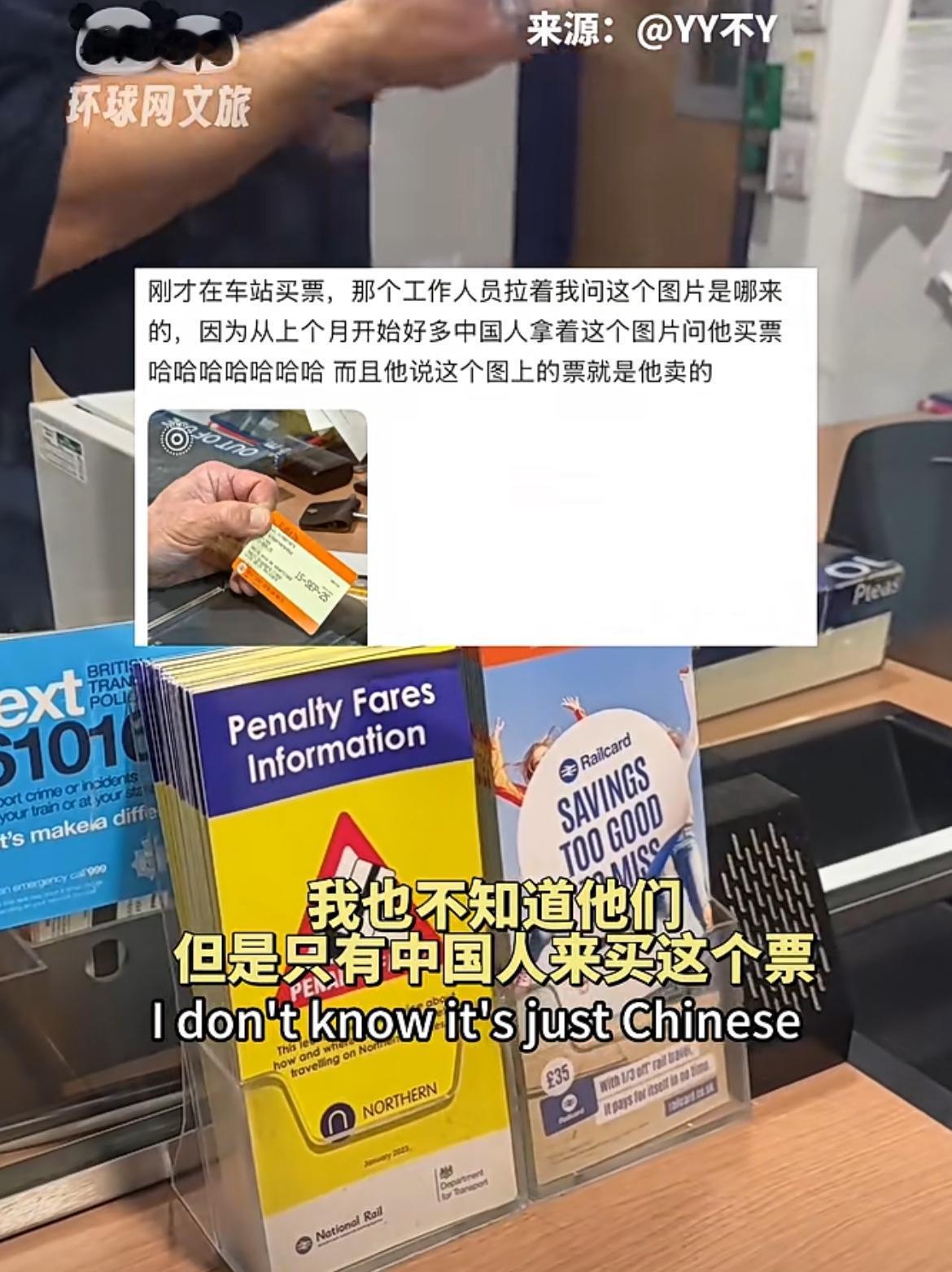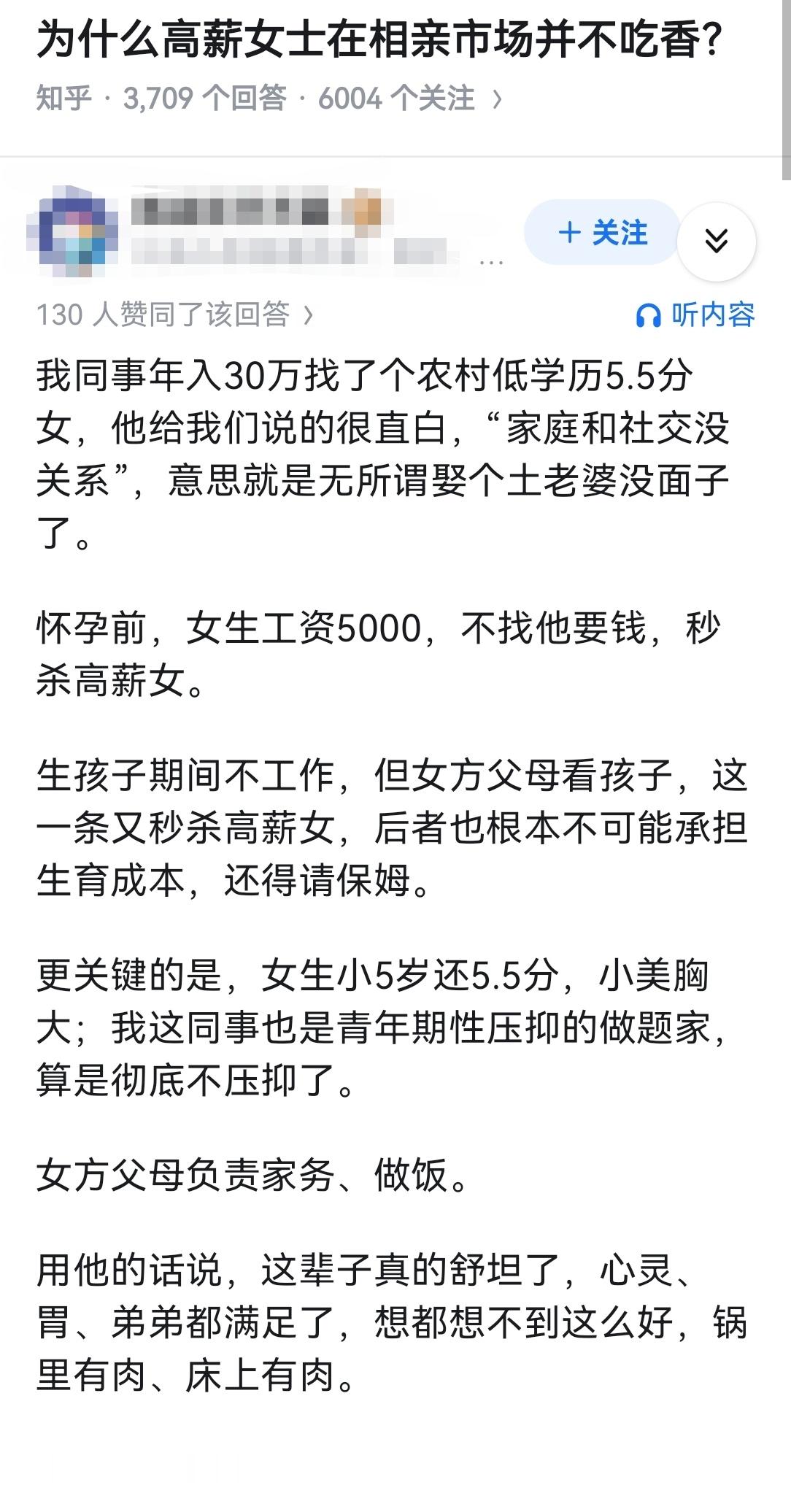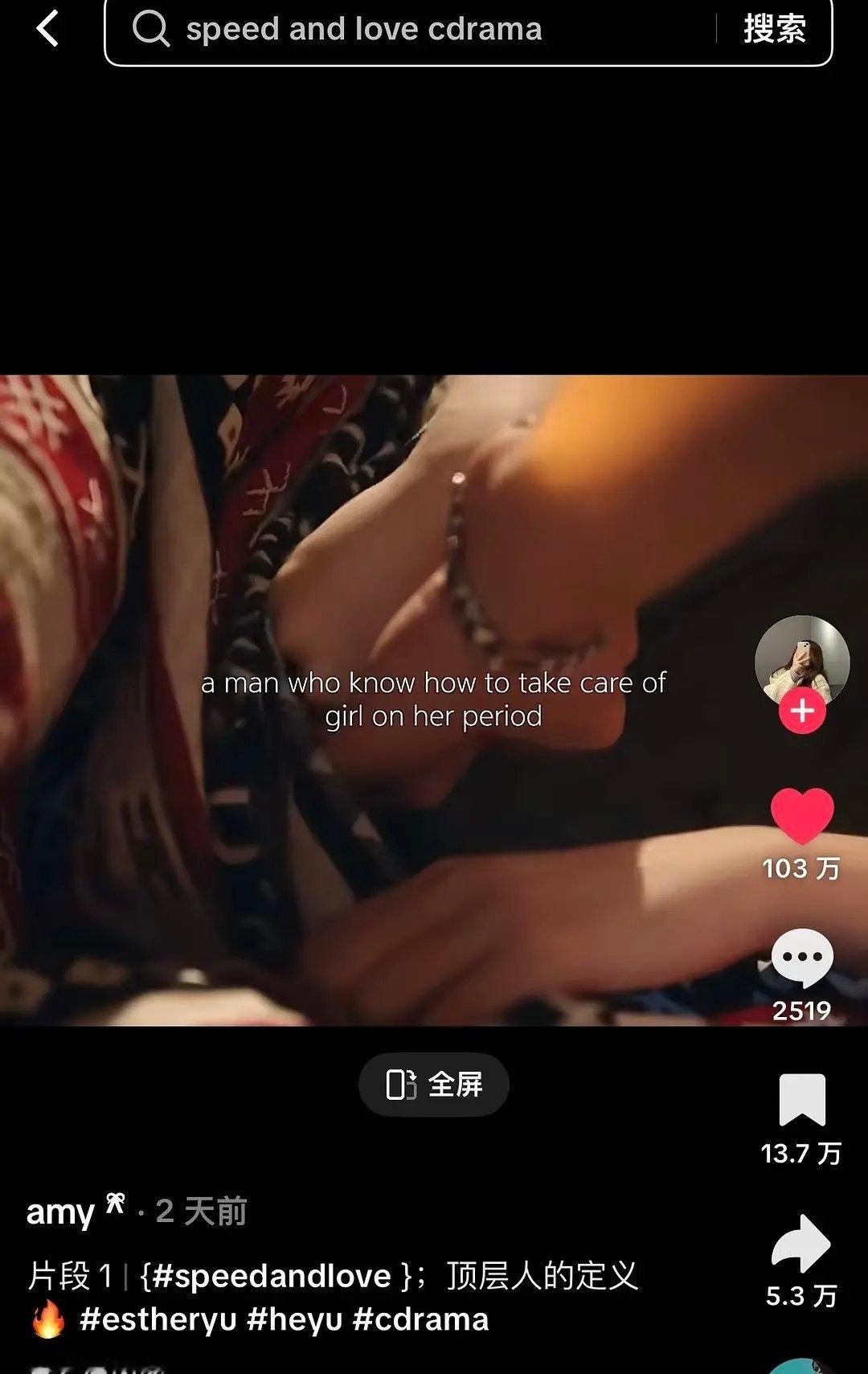哀乐声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里打转,老王捏着自行车闸的手突然收紧。 灵堂正中那幅画像,让见惯了老物件的他后颈汗毛都竖了起来。 秋老虎正凶的九月,闻喜县庄子村的这场丧事本该和晋南农村常见的场面没两样。 退休三年的老王蹬着二八大杠走村串户,车筐里装着放大镜和卷尺,本想趁着农闲在黄河边碰碰运气。 没想到哀乐引路,把他拽进了这场改变三幅古画命运的相遇。 那幅挂在正堂的元始天尊像,九阳环绕的衣袂间透着股说不出的劲儿,绢色旧得自然,不像村里画匠的手笔。 他蹲在灵棚角落抽了半包烟,终究没好意思在人家办白事时凑上前去细看。 第二天一早,老王揣着俩馍又摸回村里。 打听到画像来自村头那座快塌了的老君庙,他踩着碎砖烂瓦进了正殿。 这下看真切了,除了灵堂那幅,两侧还挂着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像。 三幅画并排挂着,线条细得像铁丝勒出来的,衣褶飘得能闻见风,颜料绿得发沉、红得发紫,倒比博物馆里那些玻璃柜里的还精神。 他伸手摸了摸绢边,指腹蹭到点细碎的颜料渣,心里咯噔一下,这质感,怕是有些年头了。 守庙的老道姓张,八十多了背还挺得笔直。 听老王问画像,手里的扫帚顿在地上:“祖师爷传下来的,民国年兵荒马乱时,师父们把画藏在横梁暗格里,上面堆着柴火,日本人来抢东西时瞅都没瞅。” 老王绕着画像转圈,发现每幅画左上角都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这是当年取下来时不小心勾住椽木挂的?”老道眼睛一亮:“你倒识货。” 后来才知道,就这几个破洞,成了鉴定年代的关键,暗格里的积尘卡在纤维里,成了百年时光的封条。 回县城的路上,老王的自行车骑得歪歪扭扭。 他想起十年前在永乐宫看到的元代壁画,当年道士们用黄土盖墙才保住那些画。 现在这三幅画还挂在漏雨的庙里,鸟雀在梁上筑巢,雨水顺着墙根往画像底下渗。 他摸出包里的鉴定笔记,翻到记着“铅丹”成分的那页,这是北宋画家用的颜料,后世很少见了。 本来想直接跟老道商量移交博物馆,但后来发现老人摸着画像边缘的样子,像在摸自家孩子的脸。 老王在道观蹲了半个月。 每天帮老道扫院子、挑水,听他讲画像怎么在祭祀时请出来,怎么用香油擦绢面防潮。 直到有天夜里暴雨,西厢房塌了半间,他才开口:“我找文物局的人来修屋顶,再请人照着画新的挂这儿,老画送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库房,中不中?”老道沉默了半宿,指着画像边角的破洞:“新画得把这几个窟窿也描上,不然祖师爷不认。” 后来博物馆的人说,这是他们见过最特别的移交条件,复制品必须保留原作的瑕疵。 现在去闻喜县博物馆,得穿过三个展厅才能看到那三幅画。 玻璃柜里的绢面在灯光下泛着柔光,检测报告说颜料里的铅丹成分和故宫藏的北宋院画完全一致。 上个月我去的时候,正好碰到修复师用棉签蘸着蒸馏水清理绢上的积尘,动作轻得像给婴儿擦脸。 展签上写着“1995年征集”,却没提那个在灵堂蹲守抽烟的退休老头,也没说横梁暗格里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但老道当年摸着破洞的手,和老王蹲在雨中看漏雨屋顶的背影,其实都藏在那些细腻的笔触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