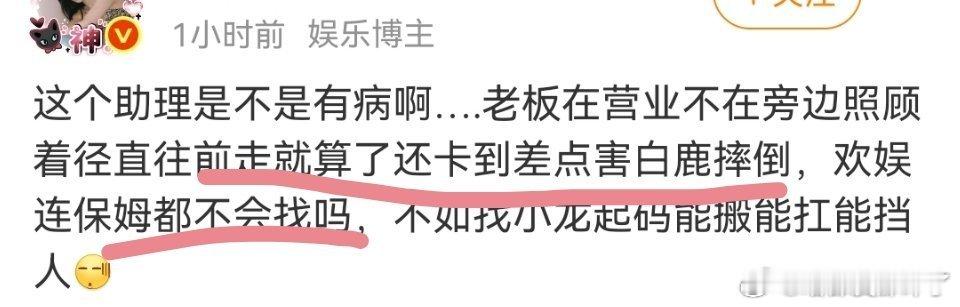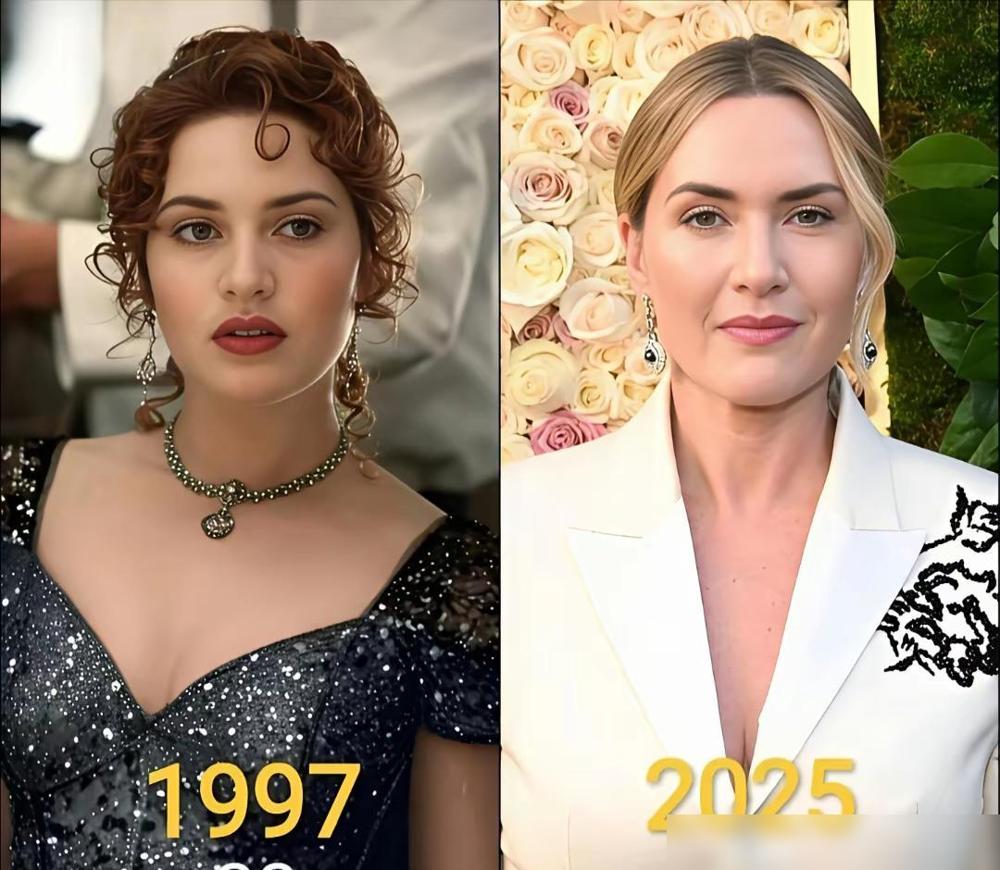1928 年,蒋鼎文坐船去普陀山游玩,途中,他遇到一个妙龄少女带了几个小孩,就问小孩:“这个漂亮姐姐,是你什么人?” 那小孩约莫五六岁,小脸蜡黄,身上的粗布褂子还打了块补丁,他攥着少女的衣角往身后缩了缩,小声答:“是俺姐姐,也是俺们的大恩人。” 少女闻言身子僵了僵,下意识把几个孩子往自己身后又拢了拢,抱着包袱的手紧了紧,指节都泛白了——那蓝布包袱洗得发白,边角缝了又缝,沉甸甸的像装着什么要紧物什。 蒋鼎文从怀里摸出块麦乳糖递给最小的孩子。小家伙眼睛亮了亮,却不敢接,只拿眼瞅着姐姐。 少女咬着嘴唇点点头,孩子这才一把抓过糖块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声“谢谢叔”。 “这包袱里究竟是什么?”蒋鼎文的眉毛拧得更紧了。他见过的宝贝多了去了,可从没见过谁把易碎品裹得这么严实还拎在手里。 这时候船猛地晃了一下,少女踉跄着差点摔倒,怀里的包袱“咚”地撞在船板上,里面传来“哗啦”一声响,像是碎瓷片碰撞的声音。 随从小李已经往前跨了半步,手不自觉摸向腰间——那里藏着枪。 少女的脸“唰”地白了,嘴唇哆嗦着说:“是……是俺娘留下的碗,路上好给弟弟们盛饭用。” 这话倒也说得通,蒋鼎文见过的珍玩多了,却没见过谁把易碎品护得这么紧,倒像是护着最后一点念想。 “你们从哪来?”蒋鼎文蹲下身,视线跟孩子们平齐。海风把他的军装领子吹得翻起来,倒少了几分官架子。 最大的男孩吸了吸鼻子:“俺们从安徽来,发大水把房子冲没了,爹……爹为了救俺们被冲走了。”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吧嗒吧嗒砸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 少女腾出一只手摸了摸弟弟的头,掌心全是老茧。“俺们要去普陀山找俺姨,听说那边有孤儿院,能让弟弟们有口饭吃。”她说到“孤儿院”三个字时,声音轻得像叹气,那年代的安徽水灾,多少家庭就这样散了,孤儿院里的每一口饭,都浸着逃难路上的血泪。 船靠岸的时候,蒋鼎文让王副官给了少女一个信封。她死活不要,说:“俺们不能白要别人东西。” 蒋鼎文把信封塞进她包袱缝隙里,板起脸:“拿着!就当是我给菩萨的香火钱,保佑你们姐弟几个平平安安的。” 少女捏着那个薄薄的信封,手指都在抖。等她拆开一看,里面竟是二十块大洋,还有张字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好好活着。” 海风吹得普陀山的钟声远远传来,她突然“噗通”跪在码头上,朝着蒋鼎文离开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撞在青石板上,发出闷闷的声响——那声响里,有感激,或许还有对这动荡年月里一丝暖意的不敢置信。 最小的孩子抱着姐姐的腿直打晃,嘴里的麦乳糖甜味还没散尽,他还不懂这大洋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刚才那个穿军装的叔叔,眼里没有别人看他们时的嫌弃。
1928年,蒋鼎文坐船去普陀山游玩,途中,他遇到一个妙龄少女带了几个小孩,就问
好小鱼
2025-12-18 15:50:38
0
阅读: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