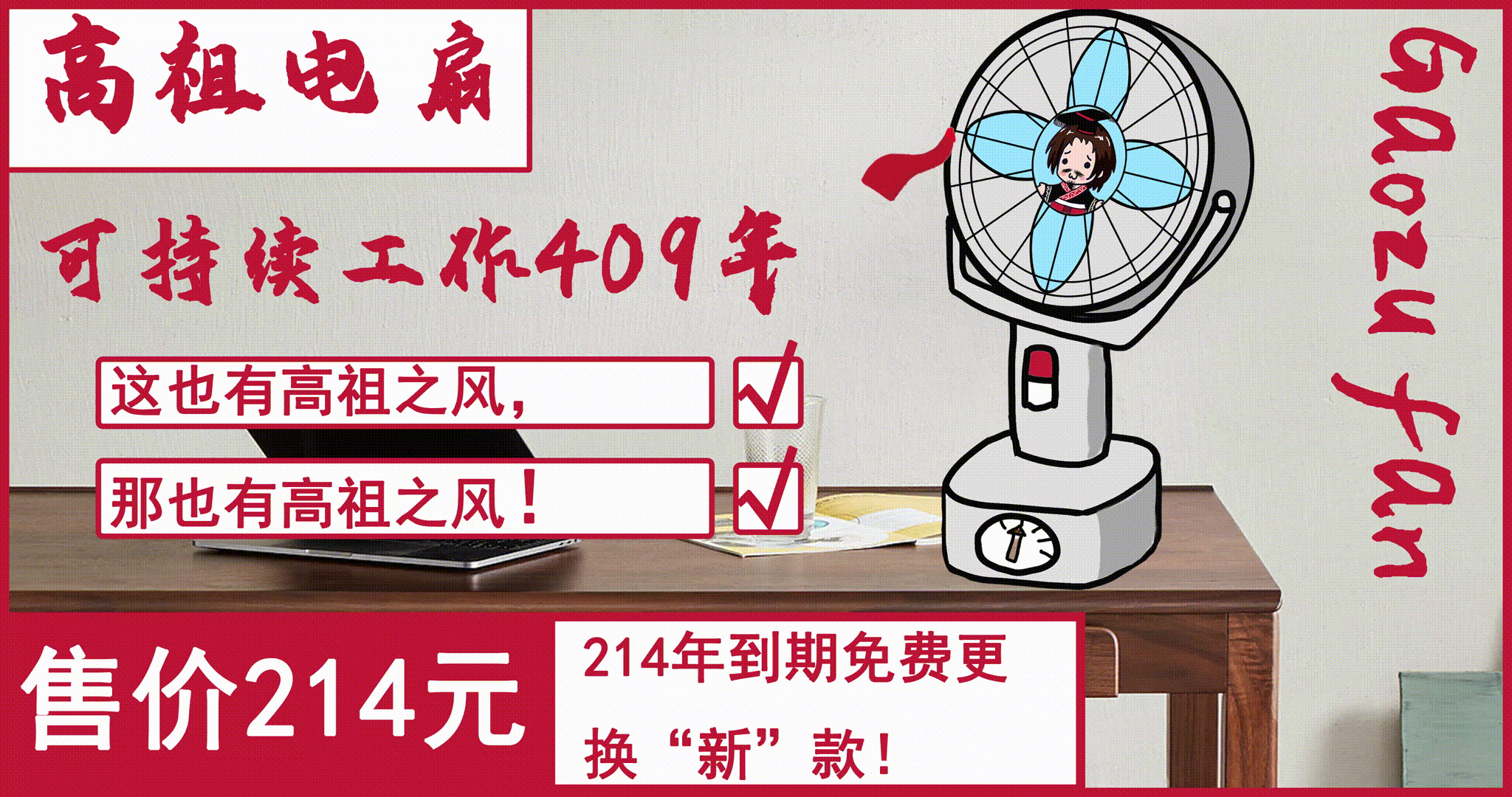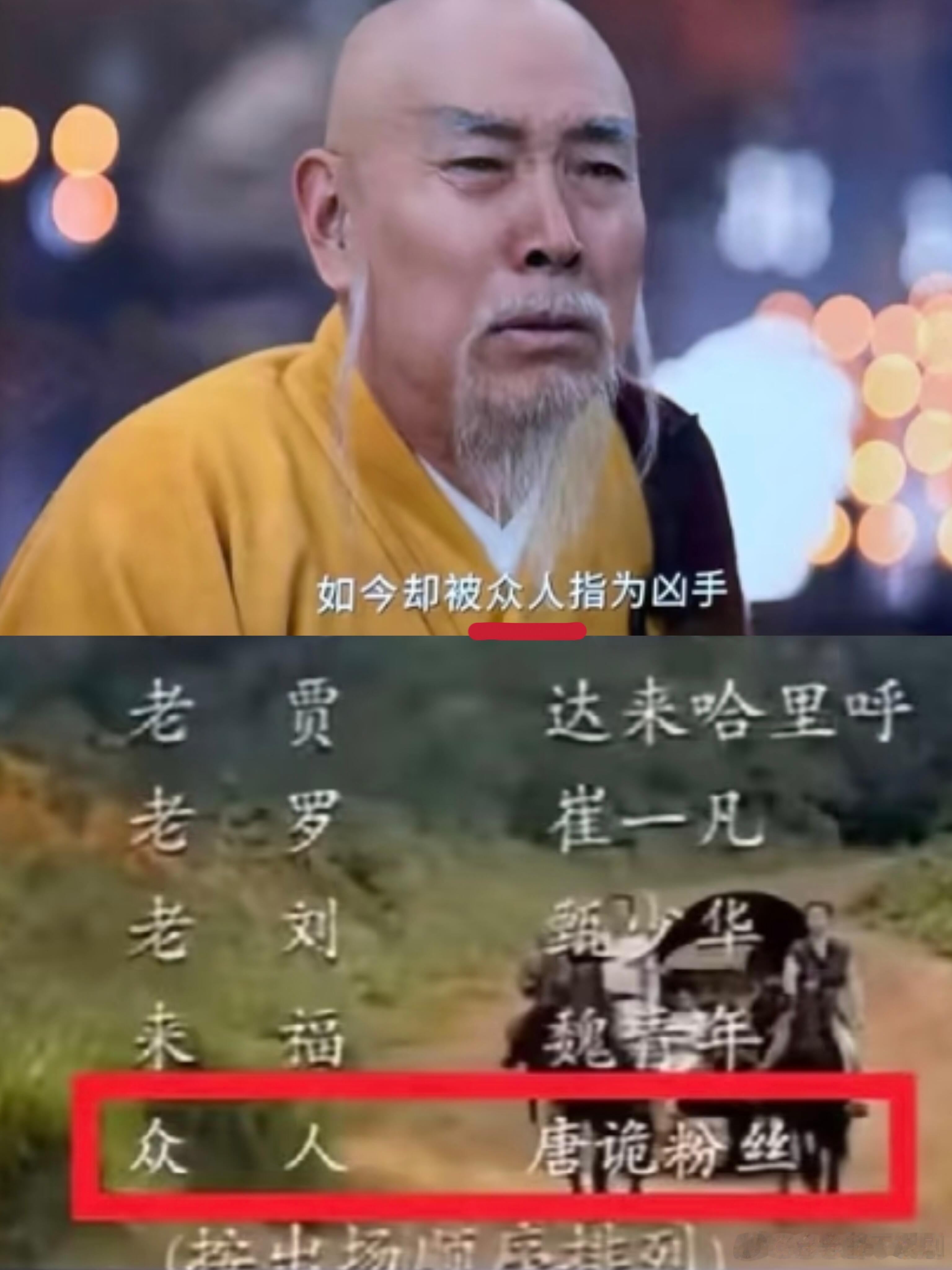这才是毛主席老人家真实照片,后面那一位有认识的吗?是不是李银桥呢?还是毛主席专用理发师周福明呢? 照片翻出来,是张旧的,泛黄边角有些卷,毛主席坐在椅子上,神色淡定,眉宇间还是熟悉的那个劲头。 可那背后站着的年轻人,有点让人犯难。 有人说像李银桥,有人又摇头,说,哎,不像,那神态像是理发的那个,周福明。 可要说起周福明这号人,讲起来就不是个小角色了。 他不是谁家老乡,也不是军队出来的干部,是毛主席身边的贴身人,既是理发师,也是警卫。从一九六零年一直干到一九七六年,十六年头,干的都不算是光鲜活,却件件都扎在了细节上,踏实得很。 时间往回拨,那年是五九年十二月底,毛主席在杭州,那天正巧过生日。 原本负责理发的师傅突发高烧,组织上怕影响主席身体,急得团团转,在城里四下里找合适人选。周福明那会儿才二十五岁,杭州市里有名的理发标兵,年轻的党员,省里还评了“积极分子”,那时候,能进党门的年轻人可不多,筛来筛去,就把他给挑了出来。 那晚十点多,领进主席房间,他心里早已是翻江倒海。 主席从房里走出来,冲他一笑,问他:“小同志贵姓?”他站直了说:“毛主席,我姓周,叫周福明,福气的福,光明的明。” 主席一听,笑起来:“名字取得好,谁起的?”他说是奶奶。 主席眯了眯眼:“你奶奶有文化没?”他摇头:“一个字不识。”主席一挑眉:“那我比她强点。”这一下子,气氛就松了。 第一次理发没用镜子,全靠他那双眼睛打量主席的神色。 他说那活儿不是随便给谁剪个头,得“瞄一眼就下手”,心不能乱,手更不能抖。 等剪完,一身汗,把衬衫都浸透了。可主席挺满意,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那年冬天,他不知道这一个头剪下去,会把自己剪进一段历史里。 紧接着,过了没多久,六零年三月八号,主席从广州回杭州,又叫他过去,说:“小周,给我理个发,跟我走吧。”话说得轻松,可一听这话,周福明差点跳起来。 那年代,普通百姓想去北京一趟难如登天,哪有那么多闲钱和机会?他激动得嘴都瓢了,一直在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主席说:“好好干。”他立马点头应下:“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从那天起,他就扎根到毛主席身边了,整整十六年。 不是常人想象的那种荣华富贵,而是紧绷着神经过日子。他们这一群人,几个月回不了一次家,孩子生了病也赶不上在身边。 家里出了事,还得靠领导人一句话帮扶。 主席知道他家孩子病了,拿出几百块钱,说:“去医院看看。”那会儿的几百块不是小数,够一般工人家吃上一阵子了。他说:“主席对我们这些在身边做事的人,很有心。 忙归忙,还记得问冷暖、问家事。” 可这份“记挂”并不是私人恩情,主席常说:“这钱不是我给你们的,是人民的钱,从我手里过一手。”他的稿费就这么支出去,谁家遭了难,谁犯了病,都能从主席那儿得到点援手。 可同时也有铁规矩,严得很:不许打着主席的旗号去外头伸手,不许利用身份谋私利。 周福明说,谁敢在外面要东西,那可真是找骂。 他们这些人,干得心里是敞亮的,规矩讲在前头,恩情也掏心窝子。 时间走到七六年,九月九号,毛主席走了。 周福明替主席做了最后一次理发,那次,他没说太多。 只是轻轻地剪,剪得很细,很慢,像是在一点点告别。理完,他又为主席扶柩守灵,一站就是好几天。那之后,他被调去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办公室,从幕后退下来,转去守着主席旧居,一直做到退休。 但他没就此歇下,后来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回韶山,也带着家人一起来。 七八趟,总归跑了。 他说韶山是主席“落根”的地方,滴水洞那边,主席晚年常去转,他每次来心情都不一样,有时候是想人,有时候是想过往,有时候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得来,像心里有根线牵着他。 他来过铜像揭幕那次,说人多得像赶庙会,还有照片留下了。 每次站在那儿,仰着头看着铜像,他都不说话,只是看着,像是把那些年全都翻了一遍。 他嘴里不说自己了不起,也从不夸自己。 他说自己就是个理发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可干这活儿得讲分寸,得有眼力。 主席信他,他就得拿出本事来。给主席理发不能像给街坊剪头那样马虎。那剪刀下去,讲究的不是个样子,而是份稳当和心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