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入世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可最终美国还是同意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为什么?江同志说,美国最终和我们达成协议,并不是突发善心。 一方面我们的实力摆在那里,他们不让我们加入也不行。另一方面,美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我们千万不能太天真! 2001年12月11日,当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正式向中国敞开,这场跨越15年的谈判终于画上句号。 当初最坚决阻挠中国入世的美国,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态度点头同意?正 美国对中国入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表面上喊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门槛,实则处处设限,可最后却比谁都积极推动协议达成,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国内那些攥着巨大利益的集团,早已把中国市场当成了必争之地。 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农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大豆、柑橘等农产品急需找到新的出口渠道,而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在他们眼里就是块“肥肉”。 为了推动中国入世,美国各大农业团体联合成立了美中贸易农业联盟,专门组建“中国作战室”游说国会,150名工作人员里有100人都来自农业领域,架势堪比一场专项战役。 他们给国会议员算过一笔账,只要中国开放市场,仅柑橘一项就能在2001年实现12亿美元的对华销售额,这样的诱惑让中西部“产粮区”的议员们纷纷转变态度。 除了农业,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制造业巨头也在背后推波助澜,微软、通用等跨国公司深知,只有中国入世,他们才能公平地进入这个潜力无限的市场,于是纷纷砸钱设立专项基金,说服国会支持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政府的战略考量,更是把“利益至上”的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时任总统克林顿力排众议支持中国入世,绝非出于善意,而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当时欧元刚刚启用,欧盟的崛起让美国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克林顿担心如果美国不主动拉拢中国,欧盟会抢先一步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那样美国将陷入被动。 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政府坚信,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贸体系,既能通过规则约束中国的发展,又能借助美国商品和文化的输入影响中国,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经济改变社会”构想。 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国入世后会逐渐按照美国的预期调整,却没料到中国会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 而且当时美国制造业面临转型压力,把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既能降低生产成本,又能让美国消费者享受到廉价商品,这种看似“双赢”的局面,让克林顿政府觉得这笔买卖稳赚不赔。 中国能在这场博弈中笑到最后,离不开自身实力的硬支撑,更离不开江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战略定力和精准决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决策直接击中了美国的核心顾虑,让他们再难拿“体制问题”做文章。 为了展现开放诚意,中国主动把平均关税从1992年的43%降到2000年的15%左右,取消了1200多种非关税措施,但在核心利益上始终寸步不让。 1999年中美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美国提出要全面开放粮食市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中国谈判代表顶住压力,最终达成了“保小麦、放大豆”的妥协。 小麦作为主粮守住绝对控制权,大豆市场适度开放,既满足了美国的部分诉求,又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谈判过程中还出现过激烈对峙,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曾因美方的无理要求拍案而起,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为了打破僵局,甚至冒着“越级”的风险直接联系朱镕基总理,这些细节背后,是中国为了国家利益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 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江同志的亲自协调指挥,他提出的“入世三原则”,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权利与义务平衡,为谈判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确保中国在开放中不迷失方向。 这场谈判的本质,从来不是谁对谁的“恩赐”,而是实力对等下的利益交换。 美国以为通过规则能束缚中国,却没想到中国不仅适应了规则,还在规则中不断成长,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美国期待的就业增长、贸易平衡没有实现,反而因为自身产业结构问题导致贸易逆差扩大,这也让后来的美国政府频频后悔当初的决定。 而中国在开放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因为入世就放松警惕,而是借助全球化的机遇提升自身实力,补齐产业短板。 江同志那句“千万不能太天真”的警示,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国际交往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美国同意中国入世,是因为中国的实力让他们无法忽视,更是因为他们想从中攫取更大利益。 中国的成功,靠的不是别人的施舍,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硬实力,是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的智慧,是关键时刻守住底线的坚定。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尊严和地位,永远要靠自身实力来支撑,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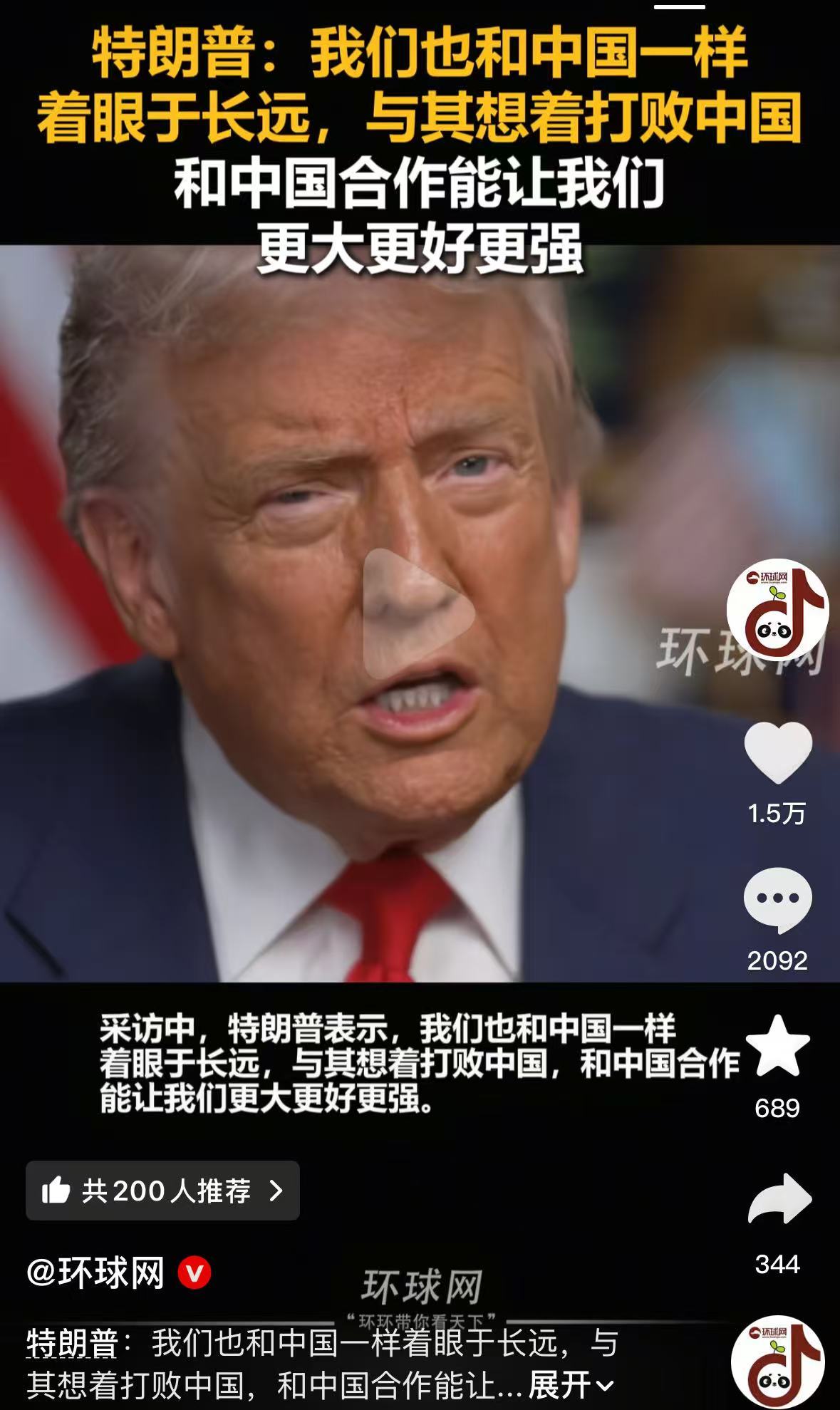



![1945年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占据整个南方区域[吐舌头眯眼睛笑]](http://image.uczzd.cn/15840328765724576423.jpg?id=0)
